网上有关“良渚文化是哪个时期良渚文化是什么时期的呢”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良渚文化是哪个时期良渚文化是什么时期的呢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1、良渚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2、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中国东南地区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类型,代表遗址为良渚遗址,距今5300-4500年左右。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在太湖流域,而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在太湖流域的东北部、东部和东南部。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另外,陶器也相当细致。
3、良渚文化遗址位于杭州城北18公里处余杭区良渚镇。1936年发现的良渚遗址,实际上是余杭县的良渚、瓶窑、安溪三镇之间许多遗址的总称。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聚居的地方。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是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代表性遗址,1959年依照考古惯例按发现地点良渚命名,是为良渚文化。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2012年良渚遗址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6年,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在中国众多璀璨的远古文化中,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是一颗非常耀眼的明珠。它以发达的稻作农业、大量而精美的玉器、精制的制陶技术、成句子的陶器符号文字资料,以及由墓葬和大型土建工程所反映出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等现象,使研究者们或者认为它正站在文明的门槛上,已看到了文明的曙光;或者认为它已进入文明社会,已形成文明古国。又因为叠压在它之上、作为后来者的马桥文化并未继承它那以独特的玉文化为灵魂的种种文化因子,故而又认为它是一支突然消失了的文化,并对它消失的原因作了种种猜测和推论。与同时期或前后时期相距不远的其他远古文化相比,良渚文化中大量的玉器以及由玉器所反映出的宗教现象、大量的非生产性支出等,的确构成了其文化的特殊性;同时,在良渚文化中,至今没有铜器遗迹的发现,对于这些究竟应如何看待?若只是简单地套用诸如铜器、文字、城址等所谓文明起源诸要素来衡量是否进入文明时代,那么,说良渚文化已形成文明,显然是要受到质疑的。考虑到这些情况,本文想通过对良渚文化中的一些现象,特别是那些特殊现象的分析,来说明良渚文化是否已进入文明社会;若已进入文明社会,那么,它究竟属于尚未出现王权的邦国形态的文明,还是属于含有王权的王国形态的文明;并进而说明它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中所具有的地位。
良渚文明研究
王震中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在中国众多璀璨的远古文化中,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是一颗非常耀眼的明珠。它以发达的稻作农业、大量而精美的玉器、精制的制陶技术、成句子的陶器符号文字资料,以及由墓葬和大型土建工程所反映出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等现象,使研究者们或者认为它正站在文明的门槛上,已看到了文明的曙光;或者认为它已进入文明社会,已形成文明古国。又因为叠压在它之上、作为后来者的马桥文化并未继承它那以独特的玉文化为灵魂的种种文化因子,故而又认为它是一支突然消失了的文化,并对它消失的原因作了种种猜测和推论。与同时期或前后时期相距不远的其他远古文化相比,良渚文化中大量的玉器以及由玉器所反映出的宗教现象、大量的非生产性支出等,的确构成了其文化的特殊性;同时,在良渚文化中,至今没有铜器遗迹的发现,对于这些究竟应如何看待?若只是简单地套用诸如铜器、文字、城址等所谓文明起源诸要素来衡量是否进入文明时代,那么,说良渚文化已形成文明,显然是要受到质疑的。考虑到这些情况,本文想通过对良渚文化中的一些现象,特别是那些特殊现象的分析,来说明良渚文化是否已进入文明社会;若已进入文明社会,那么,它究竟属于尚未出现王权的邦国形态的文明,还是属于含有王权的王国形态的文明;并进而说明它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中所具有的地位。
一、 良渚文明的特殊与一般
在文明起源的研究中,一般是以金属器、文字、城市、礼仪性建筑作为文明时代的具体标志。但包括笔者在内,陆续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1]。这一被称之为“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观,其最大的问题,一是这类“标志物”很难将它们作为统一性的共同标志来放之四海而皆准;二是我们无法判定一个社会究竟应具备几项这样的“标志物”(即在所谓文明诸“要素”中究竟应具备几项“要素”),才算进入文明时代。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里面显然有文明起源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问题。我们在考察古代世界各大文明时,每每能看到一些共同性的趋势和现象,这应该是由于它们都要面对一些共同性的问题所致。然而又由于各地生态系统、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资源条件毕竟不同,使得人们的生产形式、生活方式,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形成种种差异,从而在进入文明时代的过程中,那些被学界称之为文明的“要素”或物化的标志物也必然会呈现出差别。我们也正是通过这些差异,才可以对各区域不同类型的文明做出进一步的比较。可以说,古代不同类型的文明在其演进过程中所呈现的物化形式有同有异是必然的,而我们却非要整齐划一地规定出几项“标志物”,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事实上,各大文明古国各自的文明特征或物化的标志物都是被分别归纳出来的,上述一般认为的三项或四项“具体标志”只是一个综合的结果,是学者们从几大文明古国有同有异的现象中加以归纳、挑选、综合的产物,而对于每一个具体的民族、具体的地区来说,各自的文明现象和特征又都是寓一般性于特殊性之中的一些具体现象,各有其差异。所以,对于各民族各地区而言,作为物化层面上的文明现象即所谓的“标志物”,本质上都应是具体的、有差异的,很难抽象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几个具体标志。
鉴于上述“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观的局限性,以及实际上各大文明古国的物化的标志物都是从各自古典时期的特征归纳出来的事实,那么,我们可否不是在世界各地的横向上规定出几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志,而是在纵向上采取由已知推未知的方法,从各地各民族各自的古典期上溯到文明起源期,用它的古典时期已经完全成型的这些所谓文明的要素来作为该地文明起源期的衡量标尺?按理说,这样做应该有其可操作性。然而,这里面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是这些文明的“要素”也都有一个起源和发展的过程,它们虽然都随着社会发展的脚步而向前迈进,但它们在每一阶段相互之间的发展程度并非完全对应。以我国的商周时期为例,我们知道在商代后期和西周时期亦即古典的主要时期,被称为文明要素的青铜器、文字、都邑(城市)等都是具备的,那么是否能以这三项都具备为条件来判定中国何时进入文明时代?这也是很难说的。例如,我们用这三项来衡量二里头文化,就会遇到一些麻烦。众所周知,在我国看来,至迟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已进入文明时代,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看法。然而,在二里头文化中,都邑、铜器、文字这三项实际上只具备前两项,而且前两项各自的发展程度也是有差异的。先说都邑的问题。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遗址虽然未发现城墙,但以宫殿宗庙为中心的遗址内涵、布局和规模都决定了它的性质是都邑,这已得到学界的共识。在以往发现的属于二里头三、四期的一、二号夯土建筑基址外,近来又发掘出了属于二期的三号、四号、五号建筑基址,其中叠压在二号基址之下的三号夯土建筑基址,规模比二号大,结构也比一、二号复杂,为三进院落。因而在二里头二期时该遗址也是都邑应该不成问题[2]。一期时的二里头遗址不属于都邑,但不等于二里头文化在一期时期没有进入文明社会,这是因为此时的都邑不在二里头,在别的地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可分为容器、兵器、工具和铜饰件四类。其中容器有鼎、斝、爵;兵器有戚、戈、镞;工具有锛、刀、凿、锥、鱼钩;装饰品有铜铃和圆牌形铜饰等。各类铜器的数量不多,已报道的大都属三、四期的遗存。与二期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相比,二期只发现了小件的铜制手工业工具和一件铜铃等,二期铜器的发展程度显然难以与二期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发展程度相比拟。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时,其冶铜技术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发掘和发现才能说明问题。至于文字,二里头文化时期,除了发现刻在陶器上的一些简单符号外,尚未发现如安阳殷墟卜辞和郑州二里岗字骨[3]那样的较为成熟的文字。诚然,依据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象形符号以及良渚等文化中几个字在一起能连读成句的符号的存在,可以推论,二里头文化时期很可能已使用文字,只是现在确实没有发现。我们若是简单、机械地套用所谓金属器、文字、城市等标志来衡量二里头文化,以现有的发现而论,显然难以满足这些条件。然而几个“标志”并非全部具备,可是学术界却依然认为二里头文化时期已进入文明时代,原因何在?这主要是人们并非把文明仅仅看成是几种“因素”的堆积,而是把它看成一种社会形态,即文明社会,因而需要综合性地看问题。
在文明社会中,文明既包含有文化层面上的内容,也包含有社会层面上的内容[4]。就社会层面而论,恩格斯曾有过“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说法,一百来年国内外许多社会科学者都把国家的出现作为史前社会的终结与文明社会的开端来对待,笔者也把国家视为文明的“伴随物”,主张以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而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笔者以为,一是阶层、等级或阶级的存在;二是强制性权力系统的设立[5]。诚然,作为概念来讲,“文明”与“国家”是有区别的,“文明”不能等同于“国家”。但概念是概念,标志是标志,二者并不是一回事。以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社会到来的标志,固然主要是着眼于文明的社会属性,但它也是有其物质内容的。所以,即使仅仅从社会形态推移的角度来考察文明的起源,也每每是通过对文明社会到来时的种种现象的综合研究而进行的。而在这一综合研究中,一些较为特殊的现象,往往成为我们分析该文明具体个性的出发点。
在良渚文化中,玉器的发达是其一大特点。就其数量来讲,据统计,仅出土或传世的大件琮、璧玉器,已有上千件;良渚文化各类玉器总计,达近万件之多[6]。而良渚文化的大墓,一座墓出土的玉器也是数以百计,为此有学者提出良渚文化大墓随葬大量玉器的现象是“玉敛葬”[7]。再就良渚玉器的品种和分类而言,据林华东先生统计,良渚文化玉器的品种至少有61种之多,按其功用,可分为礼器、装饰品、组装件和杂器四大类[8]。良渚文化玉器的精美,制作技艺的精湛,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良渚文化玉器上雕刻的兽面纹和人兽结合的所谓“神徽”等纹样,其表现出统一而强烈的宗教崇拜的意识形态,更是震撼人心、耐人寻味。
面对良渚文化玉器的这些现象,从文明起源的角度看,许多学者都在“玉礼器”和“礼制”方面发掘它的社会意义。如苏秉琦先生指出,“玉器是决不亚于青铜器的礼器”[9]。宋建先生认为“良渚文化玉器的主要功能不是装饰,而与青铜器相同,也是政权、等级和宗教观念的物化形式”,因而,良渚文化的玉器,也是文明的要素之一[10]。邵望平先生更进一步指出,良渚文化那种刻有细如毫发、复杂规范的神兽纹的玉礼器绝非出自野蛮人之手。它必定是在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第三种力量支配下,由专职工师匠人为少数统治阶级而制作的文明器物。由于同类玉礼器分布于太湖周围甚至更大的一个地区,或可认为该区存在着一个甚至数个同宗、同盟、同礼制、同意识的多层金字塔式社会结构或邦国集团[11]。
在良渚文化中,作为礼器的玉器,一般指琮、璧、钺。这主要是它们的一些功用在后世的礼书和文献上有记载,尽管礼书所载的那些具体的功用不一定符合良渚文化时期的情形,但属于礼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琮、璧、钺之外,良渚文化玉器中的所谓“冠形器”和“三叉形器”,也应该属于礼器。其理由是在这些冠形器的正面中部,每每刻有或者是头戴羽冠的神人图像,或者是兽面形象,或者是神人兽面复合图像;在三叉形器的正面也雕刻有这样的纹样,而这些图像纹样与玉琮上的图像纹样是一样的,故其功用也是相同的,即都发挥着礼器的作用。只是被称作冠形器、三叉形器的这些玉器的形制没有被后世所继承,故在文献记载中也没留下痕迹。此外,在一些被称为“半圆形饰”和玉璜的正面,也雕刻有兽面纹或神人兽面复合图形。半圆形饰也称作牌饰,其具体如何使用,还不得而知。玉璜,根据出土时有的是和玉管首尾相接而组成串饰的情况来看,可判断它是作为项链佩挂在胸前的。作为串饰组件的玉璜佩戴在胸前,固然有装饰的意义,但在其上刻有兽面纹,仍然有礼神、崇神、敬神的作用。其实,正像我们后面还要讲到的那样,良渚玉礼器不仅仅具有礼神、崇敬神的作用,其玉礼器本身就是带有灵性、具有神力神性的神物,或者至少是神的载体。
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礼制的核心是贵族的等级名分制度。作为礼制的物质表现――礼器,当它在祭祀、朝聘、宴享等政治性、宗教性活动中使用时,它既是器主社会地位和等级特权的象征,又是用以“名贵贱,辨等列”(《左传》隐公五年),区别贵族内部等级的标志物,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12]。良渚文化中的玉礼器发挥着青铜礼器的功能,其使用更多的可能是在宗教祭祀当中,但它同时也告诉我们当时社会中等级和分层已出现,而在良渚文化墓葬中,凡随葬玉器、玉礼器众多者,恰恰是一些贵族大墓。所以,我们从良渚文化玉器发达这一现象,看到了它的宗教气氛之浓厚,看到了礼制和贵族名分制度的形成。
良渚文化的玉器,技艺精美,数量庞大,而玉器的制作,一般要经过采矿、设计、切割、打磨、钻孔、雕刻和抛光等多道工序,所以,制作如此之多而精湛的玉器,没有专门化的手工业生产是不可能的。这样,我们从手工业专门化生产的角度,也可以看到良渚文化玉器有着可以和铜器相匹比的异曲同工的意义。
良渚文化中没有铜器的发现,可我们也应看到,即使作为夏商周三代的青铜时代,铜器在礼器、武器、手工业工具和农具等方面的功用,也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例如在二里头文化二期,我们看到的还只是小件的铜器,到了二里头三、四期,发现有礼器、兵器和手工业工具,但各类铜器的数量并不多。一直到商代前期,还很少看到作为农具的铜器,只是到商代中期和后期,在铜矿丰富的江西新干大洋州出土有犁铧、锸、耜、铲之类的大、小型农具。应该说在铜器中最早出现的并不是铜礼器和铜农具,铜礼器只是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而作为古代经济基础的农业,在进入文明社会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使用铜农具;铜器在文明社会的初期,在农业生产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由此,在铜器的问题上,第一,铜器的使用并非每个文明实体必须具备,“文明的诞生还取决于不同的地理、经济和文化背景,历史的普遍性并不排除民族文化的特殊性”[13]。良渚文化虽没有铜器,但它的玉器却发挥了铜礼器的作用,我们从盛行玉器这一特殊现象,可以看到礼制、贵族等级名分制、专门化的手工业生产等等文明起源中带有普遍性意义的东西。第二,虽然铜器的冶炼说明了社会生产能力和技术的发展,但即使在使用铜器的地区、使用铜器的文明实体中,铜器在手工业工具、武器、礼器、农具等领域的作用,是逐步而缓慢地实现的,不能过高地估计铜器在文明初期的实际功用。
良渚文化中的刻划符号也有自己的特点。依据现已发表的良渚文化的刻划符号资料,若按符号本身划分,可分为单个的符号、几个符号连在一起构成句子的文字符号,以及几个图画符号连在一起的符号。若按符号刻在何种器物来划分,可分为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和玉器上的刻划符号。作为单个符号的,可以举出60年代在上海马桥遗址属于良渚文化的第五层出土的陶器和残片上被释读为“五”等符号[14];1986-1987年在余杭镇西的南湖出土的黑陶罐口沿内刻的单个符号,在瓶窑北湖出土的黑陶罐口沿内刻的单个符号[15];在江苏澄湖出土的有把带流罐形壶上刻的符号,在上海金山县亭林遗址出土的残豆盘的内腹底刻底符号[16]。作为二个符号连在一起的,有上海马桥遗址第五层出土的或被释为“七”“有”(ㄓ)或被释为“戊”“田”的符号[17]。还有三个符号在一起的,如1974年在余杭大观山果园出土的石纺轮,其表面等距离刻有“*”“Y”“+”三个符号[18]。作为几个符号连在一起而组成句子的,最著名的是江苏吴县澄湖遗址出土的贯耳黑陶罐腹部并列刻有四个被李学勤先生释为“巫钺五俞”的符号[19]。此外,现为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Sacklei)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黑陶贯耳壶圈足内壁刻的多字陶文[20],也是几个符号连在一起的。几个图画符号或称“图像”连在一起的,主要是余杭镇南湖出土的一件黑陶圈足罐,该罐烧成后在肩至上腹部连续刻有8个图像符号[21]。刻在良渚玉器上的符号,多为单个,也有被认为是几个符号组合在一起的。
玉器上刻的单个符号,主要是与大汶口文化陶文“炅”有关的符号,如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一件筒形玉琮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琮上都刻有“”即上边为日形的圆圈,下边为火形的符号[22]。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琮上刻有火形的符号[23]。该符号的下部刻得有点像人字形似的分开,所以,有的学者将之称为鸟纹,有的学者将之称为云纹。但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陶文中,有一个“炅”字的下部偏旁“火”,其写法与上海博物馆藏的这件琮上的“火”的形状结构完全相同,故释为“火”的符号应没问题。在余杭南湖出土的一件黑陶豆盘,中间刻有双圆圈的“日”符号,两边刻有对称的“火”形符号[24],也是大汶口文化陶文“炅”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上海福泉山5号墓出土的陶壶上刻有“火”与“日”相结合的符号[25],该符号中“日”隐藏于“火”之下,露出三分之一大小的“日”形。此外,在良渚玉璧上还刻有鸟、山等组合性的图形[26]。
对于上述良渚文化的刻划符号,学者们见仁见智,已发表了诸多见解,笔者也撰写过这方面的文章[27]。对于良渚文化中的单个符号,有的因与商周文字相联系而可以尝试释读,有的则看不出有什么联系而无法释读。但即使能尝试释读,也因其单个、孤立,看不到语言的基础,于是有一些学者认为它不是文字。尽管如此,在良渚玉器和陶器上的“炅”、“火”符号,因与大汶口文化中的同一符号相同而有其特殊意义。关于大汶口文化中的“”和“”,不但发现于山东的莒县陵阳河、大朱村、诸城前寨等大汶口文化的遗址中,也发现于湖北的石家河文化中,还发现于安徽蒙城县尉迟寺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在如此广泛的地域出现这一相同符号,说明它有约定俗成、为广大地区所乐于接受的意义。符号“”是符号“”的简体,一般隶定为“炅”,但对其解释却各不相同。笔者认为将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这些相关符号联系起来考虑,“”、“”、“火”诸形中,“火”是最基本最核心的符号。“”符号的下部是“火”形,上部的“○”既可以释为“日”即太阳,也可以释为天空星星之“星”。如果释为“星”,那么它与“火”形的符号相结合,意为辰星“大火”即大火星;如果释为太阳,在这里,这个太阳也是天象或天的代表,从而整个图形意指的也是大火星,它表达了当时的人们对于星宿大火观察、祭祀和观象授时,而大汶口文化的这类图像在良渚文化乃至石家河文化遗址中一再出现,标志着对于辰星大火的祭祀和施行大火历的文化传统,从古夷族向古越族以及荆楚之地的传播,也说明负责祭祀“大火”和观象授时的“火正”已出现[28]。
从文字起源的角度看,多个符号连在一起,其意义更大。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Sacklei)博物馆收藏的那一件黑陶贯耳壶上刻的九个符号,就其写法和结构看,也可以称为多字陶文。此陶文,饶宗颐先生考释说“乃有关古代奇肱民之记载”,并认为“是相当成熟之文字记载,与甲骨文为同一系统,其重要性可想而知”[29]。林华东先生则怀疑此陶文有可能是当年购买这件陶器时,“为利所驱使者作伪,以抬高‘身价’”,或者“可能属于一种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30]。江苏吴县澄湖遗址出土贯耳黑陶罐上的四个符号,李学勤先生释为“巫戌五俞”,即“巫钺五偶”,也就是神巫所用的五对钺[31]。张明华和王惠菊则认为,这四个文字“如果自左至右读,它们似乎记录了距今4000多年左右的澄湖地区一个以鱼为图腾的强大的部落联盟,曾经征服吞并了许多与之毗邻的擅长造船的氏族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果自右至左读,这四个刻划似乎是一个以鱼为图腾的部落曾经制造了一批玉戚的记录”。并说它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原始文章”[32]。陆思贤认为“鱼篓形罐上的陶文,是表示了渔者生产、生活的一个过程,有明确的节令概念”[33]。上引几家的解释虽然不同,但都认为它们是文字却是一致的。当然也有认为与字符化程度更高、排列比较整齐的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良渚陶壶上的多字陶文相比,吴县澄湖黑陶罐上的四字刻符,有可能不是文字[34]。笔者以为,就字符化程度而言,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良渚陶壶上的多字陶文的字符化程度的确甚高,但我们不能以赛克勒博物馆良渚陶壶上的多字陶文的字符化程度作为判断是否为文字的标准。事实上,澄湖黑陶罐上的四字刻符,除左起第一个刻符外,其余三个刻符的字符化程度已经很高了。而第一个刻符,在崧泽、良渚、大汶口等文化中一再出现,似乎已有约定俗成的意义,这种约定俗成本身已属字符化的体现,所以,不能用字符化程度的略低于赛克勒博物馆上的陶文来否定澄湖黑陶罐上四字刻符属于文字的性质。我们之所以判断这四个刻符是文字,是因为四个字符化较高的符号被并列刻在一起,使得我们可以将这四个陶符作为完整的一句话来理解,也就是说,在四个字符的背后,我们看到了其有语言的基础,由此可以证明,当时已有一些符号是被用来记录语言的,并具备形、音、义等文字的基本性质[35]。
说到字符化程度,良渚文化中还存在几个图画符号连在一起的情形,如前举的余杭镇南湖出土的黑陶圈足罐上刻的8个图像符号。对这8个图像符号,李学勤先生曾释为“朱石,网虎石封”,意思是“朱到石地,在石的疆界网捕老虎”[36]。对此,安志敏先生质疑说,把动物、栅栏和曲折线等图像作这样的文字解释,“难以令人信服,不能认为从此有了真正用文字记载的历史”[37]。林华东先生也提出疑问:“假如它的意思确实在石的境界网捕老虎的话,那么这种‘网’又是用何材料做成,何以能网到老虎?诸如此类问题,都还是一个谜”[38]。南湖黑陶罐上的这8个图像究竟应作何解释,还可以作进一步的研究,但它的确似乎是讲述了一件事情,只是因它用8个图像来表述,李学勤先生认为它有属“文字画”的可能,与澄湖黑陶罐上的四字陶文以及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陶壶上的多字陶文相比,南湖的这8个图像就根本谈不到什么“字符化”的问题,这8个排列在一起的图画,很可能是该聚落中的人用来记录某件事的不太成熟的尝试。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良渚文化单个符号中存在与大汶口文化陶文“炅”相同的符号,这不仅说明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之间的交流,也说明在这些文化中都存在着祭祀“大火”星和观象授时的“火正”与大火历。或可释为“巫钺五偶”的多字陶文,由其四个符号的字符化程度以及可以构成句子、有语言基础等条件看,应该视为早期的文字。然而,南湖黑陶罐上用8个图像来讲述某一事情的现象,又说明虽同为良渚文化,但当时用符号记录语言或表达概念的水平,因聚落而异,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性,有的已达到文字的水平,表现出已进入“中国的原文字时代”[39],而有的还停留在图画的阶段。这也说明,当时较为成熟的文字只被贵族上层中少数智者即圣者亦即巫者所掌握,所谓文字的“约定俗成”或在某一区域范围的“流行”,应当从某种特殊意义上来理解,其具体情景尚需进一步探讨。
在良渚文化中,另一个重要现象是等级和社会分层的出现。良渚文化中存在不少的贵族墓,也有相当多的平民墓。学者们依据墓葬规模的大小、葬具的有无、随葬品的多少和优劣,对良渚墓葬作出了种种划分,较多见的是划分为大墓和小墓进行对比论述。也有划分为大型墓、中型墓和小型墓三个大的等级,每一大的等级中又划出二个小的级别[40]。按照后一种划分,大型墓是指墓葬规模较大,随葬品既精美而又数量巨大的墓。它一般多有木棺,有的还有木椁,甚至出现人殉或人牲。其随葬品可达百件以上乃至数百件之多,且以玉器为大宗,同时还有少量的象牙器、漆器、嵌玉漆器,以及木器、陶器和石器等。大型墓所用玉材几乎全为真玉,集中有数量较多的琮、璧、钺等良渚玉器中的“礼器”。中型墓是指墓葬较小,随葬品只有10-30件,少数为30-40件的墓葬。中型墓多数有独木刳制而成的棺底板,随葬品以陶器和石器为主,也有少量的玉器、骨器或象牙制品及鲨鱼牙等,但玉器质差量少,琮、璧、钺等玉礼器几乎绝迹,代之而起的是陶器和石器明显增加。小型墓葬目前发现最多,不见木质葬具,随葬品大多不足10件,且多为陶器,少数有1-2件石器或玉器饰品(坠、珠等),也有的小型墓葬无任何随葬品,为一无所有。此外,在良渚文化中还存在一类被称为“乱葬墓”的墓葬。这是一些既无墓坑又无随葬品,葬式或头向不一,甚至身首异处,或是被捆绑的殉葬者或人牲。
良渚文化能划分出不同等级类型的墓葬,反映了各类资源和消费生活资料存在着不平等的占有和分配。在良渚文化中有尚玉的社会风气,玉器是一种高级物品,玉器在社会分配中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别,足以说明当时存在着社会分层。按照一位美国学者乔纳森·哈斯(Jonahan Haas)的说法,这种获取消费资料有差别应是一种方式,而不只是一个孤立的例证[41],也就是说,这种对玉和玉器不平等的获取,是与对其他类型资料的不平等获取相联系的。如果把对于玉器的不平等获取看成是对于宗教崇拜的神权资源的不平等占有的话,那么,良渚文化中的不平等获取还包括对农业的经济资源的不平等占有,良渚文化的社会分层正是以经济和神权这两类资源的不平等占有为基础的。
良渚文化墓葬材料所反映出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层,若用社会学术语或社会组织结构来描述,良渚文化的大型墓实际上就是一种贵族墓葬,大墓在各处的普遍存在,说明存在着一个贵族阶层;良渚文化中小型墓属于平民墓葬,其中中型墓是平民中较富裕者,小型墓是平民中较贫穷者,小型墓的数量最多,说明一般平民阶层是社会中的主要人口;良渚文化中的“乱葬墓”,特别是那些身首异处,或被捆绑的人殉与人牲
关于“良渚文化是哪个时期良渚文化是什么时期的呢”这个话题的介绍,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完了,如果对你有所帮助请保持对本站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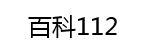 实操教程“金花大厅怎样容易赢”(原来真的有挂)-抖音官网!" data-original="http://kexinwang.com/css/1.jpg" />
实操教程“金花大厅怎样容易赢”(原来真的有挂)-抖音官网!" data-original="http://kexinwang.com/css/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