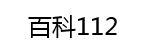对于2023年6、7月之交突然爆发的巴黎骚乱,外部世界往往抱着惊诧或猎奇的视角,重温了颇具法式特色的“郊区青年”或者“警察暴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问题的确是过去一两代人时间内沉淀下来的积弊所在,构成了当下情境中的独特挑战。
当地时间2023年6月30日,法国巴黎,警察抓捕一名骚乱者。
不过,如果把这个话题引入历史纵深,我们又会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似曾相似(Déjà-vu):那些看上去令人错愕的景象,其实在历史上不乏先例,而且程度更有甚之。仅以《谣言如何威胁政府:法国大革命前的儿童失踪事件》一书描绘的1750年巴黎骚乱为例,警民矛盾、街头暴力、郊区问题、管理弊端、谣言及其传播……种种因素都曾经出现在这座“漂浮而不沉没”的城市中,如今又改头换面,以不同的形式再度出现。应该如何理解历史与当下的相似与相异?
不宁唯是,如果再展开一个平行的视角,路易十五治下的1750年和乾隆治下的1768年,二者基本处于同一个历史横断面上,均出现了谣言扰动社会安宁、冲击政治秩序的重大事件。同属“旧制度”的两种不同体制,各自的应对手段都展示出强烈的时代和国情特征。又该如何理解同一历史时期的相似与相异?
进一步言之,中法两条平行线顺势齐下,也为今日种种异同埋下了线索。从两百多年前的遥远历史事件中,似乎可以依稀辨认出今天的轮廓,反之亦然。这种“返祖相似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切实地贯通古今,又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历史学的穿凿附会?我们不得而知,或许也并没有标准答案。但无论如何,从历史经验中寻觅答案,目的是更好地理解当下自身的处境——尤其是那些看上去充斥着混乱、暴力和疯狂的处境。
从1750年骚乱反观今日巴黎
《谣言如何威胁政府:法国大革命前的儿童失踪事件》一书的中文版,其实“入乡随俗”地更换了一个耸动标题,但法文原作标题事实上更为平和也更有学术气息——《群体的逻辑:1750年巴黎儿童绑架事件》(Logique de la foule: Laffaire des enlèvements denfants Paris 1750)。
《谣言如何威胁政府:法国大革命前的儿童失踪事件》书封
不过,如何翻译foule一词,仍然令人颇为踌躇。在中文语境中,foule一词翻译成“群体”、“人群”、“大众”或“民众”,大体都能说得通,但似乎都过于面目模糊,缺乏有机连带性。这个词的真正内涵,不仅指同一时间和空间内聚集的大量人群,而且往往由共同的目的或情绪驱动,其集体力量更大,但理性程度更低。在这个意义上,foule涵盖了一种从中义到贬义的广泛光谱,作者法尔热和勒韦将foule作为populace(“群氓”或“乌合之众”)的近义词;而在中文世界热度长盛不衰的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代表作Psychologie des foules,其中文译名《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也将其中蕴含的鄙视之情直接挑明。更为切近的一个例子,是今年三月反退休改革运动如火如荼之时,马克龙声称,“面对通过其议员发声的人民(peuple),骚乱和人群(foule)并没有正当性。”媒体和政敌很容易从这一表态中解读出轻蔑之情。
《谣言如何威胁政府》针对1750年5月发生在巴黎街头的一场骚乱,详尽考察其前因后果,从中展现了旧制度下的体制内在矛盾。细读之下不难发现,这场270多年前的骚乱,在很多方面都和2023年6、7月间在巴黎爆发的骚乱有相似性,也让人从中窥见历史的某种连续性。
1750年5月22-23日,巴黎爆发了因为“警察绑架儿童”谣言而引发的激烈警民冲突。22日,在六个不同街区分别爆发了六起冲突,警方估计骚乱人群规模达到了4000-5000人。而这次骚乱中最骇人、也最典型的案例发生在23日:一名叫作拉贝的警察试图抓捕一名11岁男孩时,遭到民众阻拦,他自己反而成了被追捕的猎物,险些被处以私刑。在警察局长向民众承诺会将其送进监狱后,拉贝暂时逃过一劫,但当天晚些时候仍然被抓住并殴打,最后被石块活活砸死。民众拖着他被剥光的尸体到警局前示威,并试图围攻警局。
这起骚乱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当时有流言称警察正在绑架儿童,送到海外殖民地充作劳动力。因此警察在巴黎街头维持秩序、驱赶青少年的任何举动,都极易引发激烈反弹。甚至仅仅是警察在街头执勤,便可能引起怀疑,进而招致围攻。
而2023年起于巴黎郊区并蔓延至全法的骚乱,起因也正是警察与未成年人之间的冲突。2023年6月27日,17岁的纳赫尔(Nahel)驾驶一辆奔驰车在巴黎西北郊区被警察拦检,但拒绝服从指令,在强行驾车驶离时遭到射杀。事件发生后,当事人的未成年身份成为尤其撩动公众情绪的焦点之一,也反衬出“警察暴力”的严重程度。
当未成年人成为社会矛盾的导火索
种种看似非理性的情绪,其实都有其渊源。在1750年之前,男孩被绑架就已经成了巴黎的一个“历史问题”,1717年一份法令曾要求将所有体格健全的流浪汉和乞丐送往殖民地,在随后几年时间里,警方为配合这项政策,不加区分地滥捕、尤其绑架流浪儿童,并因此激起过骚乱。1749年12月的一项法令试图采取强硬手段来恢复秩序,要求将巴黎街头所有的乞丐和流浪汉予以逮捕并投入监狱,并声称“这项必要的措施已经耽搁太久了”。于是,沉睡多年的记忆被唤醒,绑架儿童的流言开始愈演愈烈,最终在次年5月达到高潮。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儿童”,其含义在历史语境中和今天已经有很大差异。一方面相关标准本身就很模糊,例如在1750年事件中,被绑架的案例从5岁到18岁均有涉及;另一方面,当时法定承担责任的年龄是11或12岁(这也是整个事件中涉及人数最多的群体),而许多儿童在这一岁数之前就已经成为劳动力。虽然彼时工业革命尚未展开,童工也没有构成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但两百年前的一个12岁儿童,往往具有和今天一个17岁少年同样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意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加重要。
当事态关涉子女时,会最大程度地激发出家长,尤其是母亲的能量,以及旁观者的同理心。正如作者解释1750年事件的逻辑:“妇女对于这些绑架事件最愤慨的是它打乱了现有的社会生活。从这个角度而言……人们是否认识这些男孩都不重要了,甚至这些男孩完全是陌生人也没关系。这些绑架造成的威胁在巴黎隐约地浮现,它更多的时候打破了社会的平衡,破坏了团结一致的社会网络,它触碰到了最重要的社会资源。”
出于母性的保护本能,母亲对儿童失踪话题更加敏感,因此也更具有强大的行动力。妇女在1750年骚乱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们围堵被怀疑正在绑架儿童的警员、为孩子们提供藏身之处,在警察局长面前申诉并发起请愿,将自己的孩子描绘成善良可爱的楷模,来唤起社会的同情之心。
其中的种种关键因素,在纳赫尔被射杀后,他的母亲及家人的行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重复了当年的路径。而由此激起的社会共鸣——“这完全可能发生在我的孩子身上”——成功地掀起郊区青年及其父母的怒潮。
所谓“郊区问题”
此次巴黎骚乱再次把“郊区问题”放在舆论聚光灯下。郊区和移民群体成为各方或好奇、或斥责、或同情的对象。在这个问题上,法国左右派似乎短期内也无力再开出更强效的新药方,依然回到了“社会政策”vs“秩序优先”的老路上来,左派痛批近二三十年的历届政府都漠视郊区的贫困、隔离和绝望,最终酿成今天的苦果;右派则怒斥抢劫商店、焚烧图书馆和社区中心的“害虫”和“无赖”。而马克龙政府的当务之急,显然是倾向于后者。
然而需要看到的是,巴黎的“郊区问题”固然难解,但这种“门口的野蛮人”并不是新生事物,其本身也是老问题的新变体。从1750年骚乱(甚至更早)的历史经验来看,巴黎当时已经有了自己的“郊区问题”,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情景下呈现不同形态。
对于18世纪上半叶的巴黎来说,流动人口(尤其是乞丐)的数量大幅增长,1747-1748年的饥荒催生了一支饥饿的流浪汉大军,其中绝大部分人来到了首都,大量无业游民聚集在公共场所游手好闲、滋事生非。“在(巴黎)这个巨大平静的身躯之下还隐藏着不安分的因素……只需要一件琐事就可以打破平衡,让平静的表面泛起波澜。面包短缺、火灾或者洪灾、街头上流传的恐慌和谣言、一次庆典或斗殴都有可能成为导火索。”这构成了1750年骚乱的社会背景。
作为旁证,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也提到,1789年革命前的60年间,巴黎工人数字已增长两倍,某些地区(如圣安托万区和唐普尔区)成为贫困工人的聚居地,也成为日后革命骚动的策源地,“至于这种人口聚集会产生的真正危险,当时并无人察觉。”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起义,攻占了巴士底狱,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
而日后的法国革命,从揭开帷幕的攻占巴士底狱,一直到督政府时期的牧月和芽月暴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若干个“贫民区”(Faubourg)的怒潮所驱动的产物。而所谓Faubourg,就其字面古义来说正是“城市之外”(fors le bourg)——当年的巴黎远没有具备今天的庞大规模,核心区域只有西岱岛为中心的塞纳河两岸,如今优美雅致、看似已经完全“中产阶级化”的市区一部分(包括上述圣安托万区和唐普尔区),正是当年肮脏污秽、贫困工人混迹其间的郊区。
当然,今天再谈论巴黎等法国大城市面临的“郊区问题”,又有其独特的时代症结。和历史上郊区移民身上的经济和社会异质性相比,如今的“郊区青年”具有更多的宗教和文化上的异质性,这与大革命之后形成的普世取向的、不妥协的法式共和主义形成了更加尖锐的冲突。
但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冲突也同移民第二代、第三代的“逆反式乡愁”有关(比如用更加极端一点的例子来说,从目前曝光的案例看,近年来许多投身“圣战”的本土极端分子并不是出自真正意义的社会底层,而是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更难以忍受精神空虚之苦)。假以时日,这种逆反心态是会随着代际更替逐渐熨平,还是衍生出新的形式、激发出更高烈度的对抗,仍然需要拭目以待。但无论如何,历史维度的“郊区问题”不是自当下开始,也不会在当下结束,它只会在时间长河中不断变换形式。
恐袭阴影之下的警权扩张
许多评论在分析近年来频频发生法国警察开枪致死事件时,都归咎于2017年的法律修改放宽了警察在当事人抗拒执法时开枪的条件。具体而言,《内部安全法》第 L.435-1条规定:“当车内人员在逃离过程中可能对其(警察)生命或身体、或对他人的生命和身体造成伤害时”,警察可以向车辆开枪。
尽管法律同时规定,开枪必须是在“绝对必要并严格相称”的情况下进行,但这一条款的模糊之处仍然备受诟病。例如在纳赫尔事件中,警方一开始声称受害人曾驾车冲撞警员,但事后流出的现场却并不能支持这一说法(中对抗态势已经激化),而警方又无法提供执法记录仪的来展示冲突升级之前的状况,以证明开枪的“绝对必要”,因此落入舆论被动。
年的修法被千夫所指,但它并非凭空出现。这一举动的背景是法国刚刚在此前两年间经历了一连串恐怖袭击,其中包括震惊全球的2015年11月15日连环袭击(恐怖分子多次驾车往返于法国和比利时筹划作案),以及次年7月的尼斯卡车冲撞人群案,再加上随后柏林圣诞市场又发生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卡车冲撞事件,如何防范使用交通工具作为武器实施恐袭,就成了法国当局念兹在兹的议题。
于是,为了消除恐袭隐患(司机抗拒执法更加重了这种嫌疑),年修法放宽了警察对车辆开枪的限制。换言之,包括此次骚乱导火索在内的种种争议,某种程度上都是当初恐袭阴影的遗留产物。如果说1750年巴黎警方的执念是清除街头流浪汉和乞丐以消除社会隐患的话,那么今天的执念则是严防死守以消除恐袭隐患。
然而立法者当初修法时没有预料到的是,放宽开枪限制之后,对于防范恐袭并没有显现出明显效果(近年来法国的确曾经挫败了多起未遂恐袭,但大多是通过情报工作破获,几乎没有在道路临检时偶然发现),却导致了多起鲁莽驾车者因为拒绝服从而死于非命——其中也包括纳赫尔。
年法国警察总监署(IGPN)的年度报告称,这一年所有的警察开枪案例中,涉及射击车辆的占比高达六成。从警察角度来说,拒绝接受检查的汽车,其蕴含的风险要比一个拒绝接受检查的行人大得多,因为汽车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袭击工具,所以应对手段必须随之升级。此外,枪击事件发生后,受害者家属往往控诉警察滥施暴力,而受害者是一个邻里皆知的好孩子,以此来博得公众同情(1750年事件中也是类似的话语策略),但警察执法时却不可能具有这种视角,他们面对的是一种全然的未知:这或许是一个鲁莽的好孩子,但或许是一个正在筹备作案的恐怖分子,而面对拔枪警告仍拒绝服从的行为,将砝码更压向了后一种情况。
在这一点上,左派看到的是警察“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暴力愈发缺乏节制,右派看到的是为维持秩序而导致的“附带伤害”,固然遗憾但无须苛责。极右派更不遗余力地将事件提高到“反恐”的高度。纳赫尔事件发生后,为警察家属众筹的极右派人士,公开将开枪警察称为“巴塔克兰(式)英雄”——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此案和恐怖主义有任何关联。
此次骚乱还再度凸显出一项此前已经长期存在的安全措施的争议性,就是“根据面孔实施检查”(Contrôle au faciès)。在法国这样一个多种族聚居的社会里,有限的警力在公共场合对大流量人群进行随机筛检,外貌特征就成了最具有分辨性的指标。许多研究都表明,北非裔(阿拉伯人)和撒哈拉以南非裔(黑人)居民在公共场合被勒令接受检查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其他族裔。一项在2007-2008年间进行(亦即2005年骚乱之后不久)的实地抽样调查就显示:黑人被抽检的几率是白人的6倍,阿拉伯人则是白人的7.8倍。
这种明显的外貌歧视措施,是导致警民关系紧张、社会怨恨情绪积累的重要因素,也是2005年巴黎郊区骚乱就已经揭示出的问题。但从警察角度来说,一方面当局坚决否认在执法中存在种族歧视因素,另一方面在事实上也没有更恰当的替代手段,因为显而易见在某些特定群体中蕴含着更高风险,警方在日常执法中不可能为追求“政治正确”而对各个族群平均发力(例如几乎不可能见到针对老年白人进行抽检,尽管众所周知这一群体也是极右派的土壤)。在既有的种族紧张关系和近年来恐袭风险相互叠加背景下,歧视性的随机筛检具有很强的排斥效用,激化了少数族裔青年的反警察、反社会情绪,而这种情绪转化成街头暴力,反过来又证实了更有必要进行针对性、歧视性的筛检,二者形成了恶性循环的死结。
历史背景不同,结构性问题相似
中央集权制会出于本能地需要一个高效而强硬的警务体系。警权扩张(以及由此相关的警察暴力)问题,事实上在法国从来不是一个新问题,毋宁说它具有绵长的历史传统。从中世纪晚期以来,一整套镇压机制一直存在,并且总是在危机时刻得到充分应用。从18世纪上半叶清除流浪汉和儿童绑架事件中反映出来的旧制度下警察的肆意横行,到拿破仑帝国治下富歇建立的无情而高效的警务体系,再到《悲惨世界》中对冉阿让紧追不舍的警探,乃至1961年10月17日对阿尔及利亚侨民的铁腕镇压……可以说,数百年来的法国警民关系,尤其是警察和社会边缘人群的关系,从来没有真正缓和过。这样说不是为警察暴力辩护,而是更好地理解一个“给定”的参照系,防止落入一厢情愿的幻想。
《悲惨世界》剧照
仅就1750年的儿童绑架事件来说,其中已经显露出诸多同今日相暗合的结构性问题。
当时巴黎存在两种警察,一种是隶属于法院、具有固定辖区的commissaire de police,另一种是隶属于警察总长、没有固定辖区的inspecteur,后者属于秘密警察性质,往往雇佣社会人员作为眼线或卧底,而这些社会人员多是黑恶势力和有劣迹者,换言之,秘密警察普遍使用非正式、半合法手段来达到维持秩序的目的,但也往往因此被民众诟病。而近年来法国媒体揭露了诸多警队黑幕,例如行事乖张、羞辱当事人、同犯罪分子串通、用毒品栽赃、监守自盗等等,年的法国电影《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已经用相当克制的手法体现了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都展现出一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逻辑:1750年时,执行清除乞丐和流浪汉计划的巴黎警察局长贝里耶,是路易十五情妇蓬巴杜夫人的宠臣,这位不得人心的亲自督阵,要求在抓捕人数上多多益善,而手下则逢迎上意,秉持着“宁可错抓不可放过”的原则,频频将孩子作为抓捕目标。而基层警察的工资根据逮捕人数来发放,这也导致一些警察故意滥捕儿童,让父母花费一笔不菲的赎金才能将孩子带回家。这种滥权手段刺激了谣言的产生,也成为最终爆发骚乱的一个重要起因。
如今,这种做法改头换面,重生于两百多年后。法国基层警察一直在抱怨近年来推行的“数字政策”(politique du chiffre)。这个从未被官方承认过的非正式名称,指的是自萨科奇执政以来在警务系统推行的数字化绩效考核模式。在“数字政策”指挥下,基层警察单位要按月度或年度完成某些量化指标,例如逮捕人数或罚款金额,并将其同警员的收入挂钩(正如1750年的做法)。这样一来,警察更愿意把精力放在能立竿见影、转化为数字的工作上(比如抓捕大麻贩子),而不愿意去处理更加复杂的工作(比如处理家庭纠纷、防范家庭暴力)。尽管马克龙上台之后宣称要终结这种做法,但事实上一直积重难返。
不仅如此,片面强调KPI的“数字政策”还导致了更多的负面后果,其中包括文牍主义盛行,警察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用于填写表格、提交报告,以便给上级提供亮眼的政绩;有研究显示,基层警察的全部工作时间中,平均将近三分之二要待在办公室里处理文牍,只有三分之一略多时间外出执勤;但这些表面工夫无助于切实改善安全处境,基层警察看到今天刚刚抓过的大麻贩子,因为证据不足而被法院释放,明天又出现在街头,既导致警方和司法部门矛盾激化,又导致失去职业成就感和意义感,也成为近年来法国警队人员流失严重、自杀现象频发的间接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