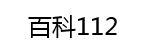第四十六章
我们就这样,快快活活每人多赚了五百元钱,咯噔,赚钱的大门就关了。差不多的晚上习惯了卸车,大家那么紧张和兴奋,突然间没了事干,人就像吹起的皮球泄了气,觉得过得没了意思。种猪和杏胡早早关门拉灯睡觉,我也坐在我的床反刍着,一边擦架板上的皮鞋一边想孟夷纯。蚊子嗡嗡地叫,你把它赶走了它又飞来,咬得脊背上火辣辣疼,放下鞋就在墙上一个巴掌一个巴掌去拍,蚊子的身子被粉碎在那里,把血流在我的手心。血是臭的,是蚊子的血臭还是我的血臭?坐在床上继续擦皮鞋想孟夷纯。我还有个孟夷纯可以想。寂寞的五富和黄八就仍然坐在楼台上说话,他们一边说着曾经在歌舞厅里发生的故事,一边乍起耳朵听楼下杏胡种猪的动静。怎么还没开始呢?他们一定这么想着。他们不睡,继续等着,就又说歌舞厅里的故事。似乎还遗憾着能记得一个两个妓女的脸,但妓女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却全然不知。
把孟夷纯从认识的那一天起所有的言语回忆一遍,把所有的动作,如头发在一转身时的如何摆动,仰头时的小耳朵和耳朵下的腮帮在微微潮红,跳上台阶的腰身,倚了门站着的有点内八字的脚,弯下腰捡东西时的屁股……哎呀,一切一切都电影似的在放映,蜜就灌满了心胸。什么时候睡着的,我不知道,好像这种回忆一直在梦里延续。
早晨起来,做好了饭,五富的门还关着,七声八声把他叫醒,五富出来瞧见种猪已端了饭吃,他说:哎,哎,你两个太不像话!
种猪说:大清早的我可没招惹你啊!
五富说:你们要干那事,就早早干,你三更半夜地才干还让我们睡呀不睡?
我把五富拉进屋,恨他丢人呀不,快吃饭上街去。
五富却将新赚得的五百元全部交给我保存,我说你应该在身上装些收破烂的钱么,他说他还有一百一十二元,蛮够了,多余钱装在身上就装了鬼,怕丢失又怕忍不住又去舞厅。
但是,我是将我的五百元带在了身上要送给孟夷纯的。
我说:五富,今日几号了?
五富不知道,杏胡说:十七号。
我说:好日子!
杏胡说:十八是好日子,十七好啥呀?
事后证明我多么正确,这一次送钱顺利见着了孟夷纯,并且与韦达正式见面了。
我虽然盼望着我能与韦达相识相熟,能成为朋友,但我们俩与孟夷纯的关系却又成了我们交往的障碍。我当然不能确定韦达和孟夷纯是不是有那一种关系,我也从不问孟夷纯,问了我害怕我心里不舒服。我问过孟夷纯是否韦达询问过我的情况,孟夷纯说没有问过。于是,我想,我和韦达都应该是好人,我们都是以各自的能力在帮着孟夷纯吧。五富曾经有一次和我谈起韦达,他说了一句:你是姐夫呢,还是韦达是姐夫?我拧过他的嘴,把嘴都扯了,他侮辱了孟夷纯,也侮辱了我和韦达。
这一次见面,我再一次认定了孟夷纯真是我的菩萨,原来我给她送钱并不是我在帮助她,而是她在引渡我,引渡我和韦达走到了一起。
在美容美发店的巷口,孟夷纯和韦达站在那里说话,我的出现孟夷纯首先是看见了,她给我招手,快活地叫:快来,快来啊!而韦达这时也看见了我,他一下子庄严了,礼貌地给我点头。他点头的时候右手按在腹部,微微弯了下腰,微笑着。我当然也文雅了,说:韦总你好?他说:是刘高兴吗?我说:是刘高兴,他说:又看见你了,真好!但他却要告辞。这让我有些意外,他不愿意和我多呆吗?不愿意让一个熟人看见他和孟夷纯在一起吗?孟夷纯说:你要走呀?他说:对不起,刘高兴,你们是乡党你们聊吧,我还有点事。孟夷纯说:不行,谁都不要走!好不容易你们又碰上了,我还有话要给你们说的。孟夷纯就拉了我们往马路对面的一家茶馆走,她说:我请客!
在茶馆里,孟夷纯把韦达的公司给我作了详尽的介绍,她也把我怎样拾破烂,又怎样把拾破烂攒下的钱都给了她,统统地都说了。
韦达就惊讶地说:是吗,是吗?
我说:我还不是在学你吗?
韦达手指着自己:学我?
我说:夷纯给我说了,你一直在帮她。
韦达说:还不是为了尽快让她筹集破案费吗?
孟夷纯说:我在西安城里,待我最好的两个人就是你俩了,我提议,你们应该拥抱一下吧。
我和韦达拥抱了,韦达的双手在我背上拍,怀里的墨镜硌着了我,我现在是不敢把墨镜掏出来了。我也是把他用力地搂了一下,我吃过豆腐乳,怕他闻着了怪味,把头侧向一边。我又一次感觉到了他的心跳,也感觉到了他的肾跳,是肾跳,他的那个肾和我的另一个同样节奏地跳。不呀,我的双肾在跳。我看见了茶桌上一盆花在微微地颤,是兰花。
孟夷纯站在一边,她的眼睛眯着,有一种狐气,安静地注视着我们,后来就轻轻拍手。
谢谢你,孟夷纯。如果不是孟夷纯,我怎会见到韦达呢?茫茫如海的西安城里,我的两个肾怎会奇迹般相遇呢?韦达是何等的有钱和体面,我们拥抱着,这一幕为什么五富没看见呀,黄八杏胡种猪没看见呀,还有韩大宝,我的侄儿……清风镇的人都在这儿就好了。
嗨,刘高兴呀刘高兴!我在心里却又叫着我的名字,我以为你是早觉得应该是城里人,你拿势着,骄傲着,常常要昂首行走,有时还瞧不起韦达和有钱的大老板,其实,那是你故意要那么做的,韦达这么一拥抱,你才知道自己真的是乡下人,是城里的拾破烂的。
我推了推韦达,我俩分开了。
我拍打着我身上的土,也拍打了一下韦达身上沾着的我的土。
何必呢,刘高兴,这又是你的自卑和委琐了不是?韦达在看着你,他的眼睛依然温和,他向你又伸过手,把你的手抓住了,拉你在椅子上坐下,你如果再拒绝,或者迟疑,那就是你真瞧不起了你自己,那才是你和五富黄八是一样的货色。把头抬起来,看韦达的眼光,你们是城里的一对兄弟!
你是在哪条街上拾破烂?韦达关切地问我。破烂好拾吗,一天能收入多少?辛苦呀!
我回答着韦达。拾破烂辛苦是辛苦,天上是掉不下肉饼的,干什么事不辛苦呢?韦达的西服真挺。我说我见过一些老板,做房地产的,做药业的,做外贸的,做投资的,他们虽然开着小车,带着秘书,出入于豪华宾馆酒店,但我在家属院拾破烂的时候,看见过他们傍晚回家时的疲倦劲,听他们家人诉说过压力。韦达戴了一块什么表?右手腕上还有一串佛珠,他信佛吗?你韦达不是也头发稀薄吗,眼圈也发黑吗?年龄并不比我小多少吧,脸色除了白外,皱纹可能比我多吧,还有肾……我说我在兴隆街十道巷那一带拾破烂,平均收入每天十几元吧,挺好的。说不说破拾钱夹的事呢,说不说肾的事呢?还是不说破的好。韦达微笑地给我点头,他说:你说话怪幽默的。我不好意思了,是幽默,但韦达沉稳。你抽纸烟吗?我来一根吧。我起身接纸烟的时候,手先是撑了一下腰,腰怎么又不舒服了?还是不要说破。我知道就是了。
现在。是孟夷纯在说话了,她开始表扬了我的优点,比如聪明,能干,善良,可靠,还有,她在说我长相清秀,有气质,如果我不蹬着三轮车,谁也看不出是个拾破烂的乡下人,说我是不显山露水,说我是藏龙伏虎,说我绝不是地上爬的卧的角色。她这么说,我有些窘。别人说你好话和一个醉汉给你说话是一样的,你既不能附和也不能反对还得认真听着。孟夷纯终于说出她的目的了,她说:韦总,刘高兴怎么能不辛苦呢,何况拾破烂能赚多少钱呢,你能不能让刘高兴也到你们公司去干个事儿?
韦达哈哈大笑,说:孟夷纯原来要给我下任务哟!
孟夷纯说:就是的,得求你!
我赶紧摆手,韦达已经在问我:你干没干过推销?
没。
财务呢?
没。
有什么技术?
我只能下苦力。
韦达低头想了一会儿,说能不能去公司看大门呢,那活不重,就是二十四小时都离不得,不知道你能不能坐得住?我可以把现在的门卫辞退,一月给你六百元,愿意不愿意?
孟夷纯先高兴起来了,她扳着我的肩,说你怎么会坐不住呢,六百元就六百元,干得好了,韦总肯定还会加薪的。
我说谢谢韦总,但是。我说了一句但是。
孟夷纯说:你说什么?
我说:我是和五富一块来的,他没出过门,处处得靠着我,我要是去了,他一个人拾破烂我不放心。我拿眼睛看韦达,韦达说门卫安排两个人不合适。
我说:能让五富干些别的活吗?
韦达明显地为难了。
孟夷纯在瞪我。对不起,孟夷纯,这事我不能听你的。我回在孟夷纯和五富中间倾向了五富,我不能重色轻友。
是这样吧,我给韦达说,你让我安排安排五富,如果能把他安排妥了,我立马就去公司,实在抱歉,也让你见笑了,我和五富是一块出来的,我得对他负责。
韦达始终在微笑着,他赞赏了我的想法,然后他就告辞走了。韦达一走,孟夷纯又埋怨我。我说:你不能逼着人家给我寻工作么。孟夷纯说:他那么大的公司,安排一两个人算什么呀。我说:他是不是不想让我去?孟夷纯说:人家可是一直笑着让你去的么。我说:就因为他老笑着。他明知我和五富两个,却只让一个去,让我看门,我肯定是坐不住,又只是六百元钱。他知道你把他和你的关系告诉我了吗?孟夷纯说:啥意思?我说:他是不是不让我知道什么,在我面前才一派和气又那么正经?孟夷纯说:你心思就是多!
孟夷纯说这话的时候,她拿指头戳我的额。我就乖乖巧巧地让她戳,然后掏出五百元给她。她收了,还再戳了一下,说:小心眼!
小心眼就是小心眼。我问:公安局那些人走了?她说:我向我老板借了一千元,打发他们回县了。我们就再没有说话,她把五百元抽出一张又交给我,我再把一百元又塞进她的口袋。
第四十七章
我是到底没有去韦达的公司,因为五富他真的离不得我。我已经说过,前世或许是五富欠了我,或许是我欠了五富,这一辈子他是热萝卜粘到了狗牙上,我难以甩脱。五富知道了这件事,他哭着说他行,他可以一个人白天出去拾破烂,晚上回池头村睡觉,他哪儿也不乱跑,别人骂他他不回口,别人打他他不还手,他要是想我了他会去公司看我。他越是这么说我越觉得我不能离开他,我决定了哪儿都不去,五富就趴在地上给我磕头。
起来,五富,起来!我说,你腿就那么软,这么点事你就下跪磕头?去,买些酒去,咱喝一喝!
五富是提了整整一大捆子啤酒,他几乎将他几天的收入全都买了酒,把黄八和杏胡种猪都叫到他的房间来,说是他过生日,放开喝,往醉里喝,往死里喝。我们就都喝高了。五富要去上厕所,去了半天却不见出来,我以为他醉倒在厕所了,过去看他,他真的坐在厕所地上,立不起身,而手里还提着一瓶酒。他说,高兴,兄弟,我没啥报答你,我喝酒,我把我喝醉……
我说:你已经醉了。
不,我还要喝!他举起瓶子咕嘟咕嘟往嘴里又灌了一阵。高兴,我不是女的,我要是个女的我就让你糟蹋了我,我不是女的,我就让我难受来报答你,把胃喝出血了报答你!
我把啤酒瓶夺了,背着他出了厕所。
我没有去韦达的公司,孟夷纯当然有些失望,但她并没有再说什么。我依然隔三差五的中午时蹬着三轮车去看她,她有时在美容美发店,有时不在。不在的时候我就在店对面那堵墙上用石子划道,这是我们约定好的,她可以知道我来过。只要在,她跑过来手里肯定端一个茶缸要我把一缸茶水喝完。茶缸上有口红印子,我说:我从口红印处喝。她只是笑。
我问:有什么进展吗?
这似乎成了习惯性的问话。先是孟夷纯还给我说点抱怨的话,后来就不再愿意提说这样的问题,她有些躁:你烦不烦呀?!给我一张憔悴的脸。
我不怪罪她,只是满怀地去看她,走时心里像塞了一把乱草。
几时才能破呀?我不清楚她到底能挣多少钱,而韦达和她的那些老板们又能给她多少钱,而我给她的钱又能顶什么用呢?想起来,这是我最难受的。开初我去送钱,感觉我像古时的侠士一般,可破案遥遥无期,我再去送钱,没了那份得意,而且害怕在把钱交给她的一瞬间她脸上掠过的一丝愁意,虽然她依然在笑,在说着感念我的话。
我说:或许很快就破了哩。
她说:我怎么就害着这么多人……
这期间我想到了我去一次她的家乡,去追问和催督公安局,和公安人员一起去破案,但这些想法又怎么可能办到呢?我甚至也想到我用纸糊个箱子沿街去募捐。当给孟夷纯提说我的想法时,她哭了,说韦达也曾想过把她的情况通报给报社,她拒绝了,那样或许全社会会募捐一些钱,但也同时社会知道了她的身份,即便是案子破了人们又会怎么看她呢,一切只能暗中筹钱。
可这么筹钱又筹到几时呀?!
我准备把这事告知给五富黄八和杏胡夫妇,希望他们能想些办法。虽然孟夷纯早已是我的菩萨,但他们若知道了孟夷纯的身世,又哪里肯相信一个妓女能是菩萨?我琢磨了几天,琢磨得头疼。于是我以去塔街办事为由领他们去了一趟锁骨菩萨塔,给他们讲述了锁骨菩萨的故事然后说出了孟夷纯的困境,他们就都叹息了。
杏胡说:叫什么名字来?
我说:叫孟夷纯。
杏胡说:是不是你曾经给我说过的早上起来想到的那个人吗?
我说:是她。
杏胡说:你为什么不领她来见我?
我说:我不好意思。
杏胡说:我只说我是苏三的苦,没想还有个窦娥的冤!你准备咋办?
我说:我得求你想想办法。
杏胡说:那我知道了。
杏胡是几次和五富、黄八商量,最后达成的协议是:每人每天拿出二元钱,让我转交给孟夷纯。让五富黄八和杏胡出钱,这并不是我的初衷,但杏胡的权力和能力也只能让五富黄八连同自己来捐款,每人每日二元钱数字并不大,却说明了他们对我和孟夷纯的认可和支持。从那以后,每天晚上杏胡就像个收电费的,她抱着那只曾经装过小米的陶罐儿,挨个让大家往里塞二元钱。我也塞了二元钱。杏胡和种猪是一家人,本来只出一份,而种猪犹豫着,还是再塞了一份他的。
我称他们是我拾破烂的朋友,多感激这些拾友!平白无故谁肯给你一分钱呢,去商场里买货,去饭馆里吃饭,少一分钱你能买到一根针吗,能吃到一碗面吗?
五天后,我把他们的捐款五十元交给了孟夷纯,孟夷纯却给我大发脾气。
她说:谁让你把我的事说给他们,你是要让全西安的人都知道我是妓女吗?我就是妓女!我不需要你的那些人同情!我哥做冤死鬼就让他去做冤死鬼吧,这案我也不破了!你不要再来找我!你给我的那些钱我会还你!一分不少地还你!
她语无伦次地嚷着,接着就嚎啕大哭。我当然觉得委屈,还要解释五富黄八杏胡夫妇绝没有笑话她的意思,孟夷纯还是把钱扔给我,推我出门,她就把门严严实实关了。
孟夷纯怎么会是这样?这种偏执和歇斯底里的性格以前我没有发现呀,或许她隐藏的这种性格正是她走到这一步的原因,她和那个杀人犯,也是她的男友就这样而导致了分手,也使她在案发后又走上了妓女之途吗?
孟夷纯的心里,还是压根没瞧得起我吧。
为什么呢,如果她已经认我是自己人,她是不会这样对我发火的。我想起了曾经做过的那个梦,她还是仅仅把我当一个朋友看待的,她给我说她的身世,可能是以她从县城来到西安的身份而滋生了对我倾诉的欲望,肯继续和我交往,可能是我还能和她说到一处,我们有共同的语言。而一旦事情发生了她认为损害了她利益,她就像含羞草一样收缩了,自私了,全然断绝了外界。
孟夷纯,你这样会伤害感情的。
或许孟夷纯对我就没有感情,孟夷纯对任何人都不可能有感情了。
我离开了孟夷纯租住的那座楼,满街的树开始落叶,我没有吹箫,也不吆喝,蹬着三轮车一到兴隆街的十道巷口,一屁股坐在地上,什么也懒得动了。
十道巷口有一棵百年核桃树,树上落下的花絮,如一地的毛毛虫。核桃树落花絮,夏天就要过去,天气该慢慢地凉了吧。怎么把事情弄到了这步田地呢,城市生活咋就把我像打着的一块铁,一会儿塞进了火里一会儿又扔到了水里?我盯着核桃絮,核桃絮真的成了毛毛虫,蠕蠕地似乎向我身边爬来。
喂,刘高兴!
有个戴眼镜的在叫我。我认得他是前边的一个家属院的,他要我把三轮车蹬到家属院的五号楼下,他有旧书刊卖给我,说完自个就先走了。戴眼镜的一般都是有知识的人,知识分子从来不和凡人说话的,我也没多问别的,待他走后,搓了搓脸,使自己活泛起来,推三轮车去了五号楼。
我是把三轮车停在五号楼下已经多时了,却不见他下来,等到下来了并没有拿了什么旧书刊。他说坏了,钥匙忘在屋里了,门开不开,问我能不能从窗沿上爬过去翻进屋里。我随他上到四楼,而从那么窄的窗沿上爬过去推窗入室,我不敢。那人急得火烧火燎,我说:我帮你开门。
你带了吗?
他没带,我就在我的口袋里找,我的是装在身上的,因为街上的警察一看见蹬三轮车拉架子车的就时常要检查的。
他说:拿开门?
我告诉他,我是听我侄儿说过,用塞进锁子边的门缝处,一边摇门一边往里塞,是能开了门的,但我从未开过,咱们试一试。我就那么试着,竟真的把门打开了,我们都很高兴,他抱出一大堆旧书刊卖给了我。
我是把旧书刊刚刚抱下楼,另一个门洞的那个老太太用自行车驮了一袋米过来,这老太太每次见到我总给我笑笑,我一直对她有好感,就说:你老买米啦?她说:啊,买了米。我说:有人给你掮上楼吗?她说:我等孙子回来。我帮她往上掮,她的家在七楼,掮到了,她说:你是哪里人?我说:商州的。她说:噢,那地方我去过,苦焦得很。我说:还可以。她掏出二元钱要付我,我不要。帮着掮一袋米还收人家钱吗?她说:你不收我就欠你的人情债了,你得收下。这话多少让我听了不舒服,她不愿落人情债,那我帮她的好心就全没了,说起来掮一袋米到七楼也不值二元钱,可如果你要掏二元钱让我掮米袋到七楼我还不愿意掮哩!
我走下了楼,那个我帮他开门的人正和另一个人说话。一个说:教授你把钥匙忘在家了?一个说:可不。一个说:那咋开的?一个说:那个拾破烂的帮我开的,他拿在门缝里塞,塞着塞着就开了!一个说:拾破烂的能开门?他可是常到咱这院子来的,这得防着啊!一个说:人挺老实的。一个说:老实能会用开门?!
我一下子愤怒了,说:你们可得把门看好呀,小心让我偷了!
那两个人显得很尴尬,相互看了看,进了门洞不见了。我往院子门口走,发誓再不到这个家属院来了,而老太太却小跑过来,还是一定要给我二元钱,我头不回地走,她在后边说:哎,哎,你让我一看见你就觉得心亏吗?
我离开了家属院,把车子蹬到大街上。清风镇有纵纵横横十多个巷道,从哪一个巷道都可以进镇,巷道里你看见了那个帽疙瘩鸡就知道是谁家的,那个撅了小尾巴要拉屎的母猪也知道是谁家养的,那个老头过来了,脖子上架着一个小孩,这老头的亲家是麻脸还是秃头,架着的小孩是孙子还是外孙,你心里明明白白……想这些干啥?谁也没把你用绳子捆到城里来?!到了城里就说城里话!我原准备把三轮车停放在花坛边上,坐在那里要吸一根纸烟的,前面有了警察,又把三轮车蹬到一堵矮墙下,坐下发闷了。
孟夷纯。我怎么一坐下来,脑子里还是想到了她。
好事现在是很难做的,孟夷纯就告诉过我,在街上有人看见有抢妇女的手提包而见义勇为去追抢匪,结果被抢匪戳了一刀,有人把街头受伤昏迷的人抱去医院抢救未救过来,而死者家属到医院后却抓着那人不放,说是他致伤的。我帮忙开了门,会不会那幢楼上所有人家要重新换防盗门呢?老太太的话是对的,她掏了二元钱,她不欠我的人情债了。在清风镇可能是靠情字热乎着所有人,但在西安城里除了法律和金钱的维系,谁还信得过谁呢?
你怀疑孟夷纯对你没感情,对所有人没感情,那孟夷纯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还和你交往,是看上你那点钱吗,你那是多少钱?!真是小心眼,而且太敏感!还有,刘高兴,为什么你给孟夷纯送钱,为什么每次送给孟夷纯钱了就得意?你是在孟夷纯困难的时候才觉得你不是个拾破烂的而是个英雄!还记得曾经做过一个梦吗,那是你在对一棵树说话,你说:最好永远都在破,又永远都破不了。什么意思?希望她永远是弱者,比你还弱,你就能控制她?卑鄙呀,卑鄙!
那一瞬间,我醒悟了孟夷纯为什么那样反感我把她的事告诉了五富黄八和杏胡夫妇。
我决定了还要去找孟夷纯,她的事我有责任为她守密,我检讨我的敏感多疑和脆弱,我再去送钱绝不对她有别的要求,她就是主动和我怎样,我也不,一切都到案子破了再说吧。
第四十八章
要想案子尽快破,我只有多。我想到了杏胡说的良子的情况,就和五富去找了一趟我那侄儿。
良子果然混得比我好,他每日送煤卖煤的车就不是架子车,也不是三轮车,威风着哩,是三轮摩托货车。这家煤场是山西人开的,煤场里堆的煤炭像山,六台煤球压轧机一排儿摆在那里,凡是来买煤的当场压轧成煤球,良子便开车送去,没有买主了,又装上一车沿街去叫卖。良子送煤卖煤已经很有名了,他有名片,上面写着:煤球王。
煤球王对我和五富的到来显得不热不冷,引我们到他的住处后去买了一盆酸菜鱼,又买了一筐蒸馍。这是一间仅有六平方米的棚子,后墙就是院墙,棚顶也是一块塑料板,从院墙上斜着搭过来。棚子里有床,一个煤炉子,一条绳在墙角拉着,挂着一件西服,竟然还有一条领带。
我和五富希望在煤场送煤卖煤,煤球王首先反对,他也警告甭找老板,因为老板之所以听他的,是他已经控制了所有送煤的单位和私人用户。知道《林海雪原》中的栾平吗?他说,栾平手里有联络图,我就是栾平。这小子完全不认六亲世故了,但同意我们白天去拾破烂,晚上可以批发一些煤球到东新街的夜市上去卖,这个夜市也属于他管辖。
煤球王在家时学习并不好,也看不出有什么过人处,而到了西安竟出息得没有他不懂的。他领我们去东新街夜市,那里多是卖牛羊肉泡馍的。他问:你们谁晓得秦国为啥打败六国统一了天下?我说:你以为你读过初中?我还是高中生哩!他说:为啥么,说!我说:秦国有个秦嬴政!他说:看来是不晓得,那我给你们解释一下。他说秦国人爱吃牛羊肉泡馍,战场上,秦国人背着牛羊肉背着干饼子就出发了,兵贵神速,所到一地很快就做饭吃了,而那六国人没有牛羊肉泡馍,才淘米呀,洗菜呀,七碟子八碗地吃呀,秦国人已经杀进营了。秦国人打败六国是饮食打败的!我说:噢。他就骄傲无比,从口袋掏了一盒纸烟给我和五富各散一根,他自己嘴里叼了一根,不用手,纸烟能从这个嘴角主动移到那个嘴角。瞧他的那个样子,我就没有点燃我的那根纸烟。东新街的夜市,阵势非常大,一部分是有门面房的,每个门面房也就那么一间两间,入深浅显,而更多的则是将摊位支在路边,每个摊前拉个电灯泡,摆一盆洗涮水,摊主就戴顶小白帽,肩上搭条毛巾,吆喝着买卖了。煤球王又给我们讲了,讲中国有八大菜系,西安是没有菜系的,为什么,因为西安是十三朝古都,皇帝在皇城的时候,全国各地都要把他们的菜拿来竞赛,西安就如同是一个大饭桌,各类菜都来摆,慢慢自己就没有什么大菜了。而没有了大菜,小吃却丰富了起来,这就是现在夜市上的羊肉泡、葫芦头、柿子饼、肉丸胡辣汤、粉蒸肉、卤汁凉粉、油泼面、大刀面、涎水面、摆汤面、凉皮、甑糕、麻食、油茶、汤包、油塔。他讲得我们一愣一愣的,五富说:不得了,他咋知道这么多!我说:别附和他,附和了他就逞能得没完没了,人来疯!果然他说着我们都不接应,他就不说了。但我得承认,这小子确实在这里很熟,摊上的人似乎都认识他,说:煤球王今日不卖煤啦?他说:他两个替我卖的,以后多照应啊!人家说:哈,雇小工啦!
小吃摊上是需要煤,但要量很少,他们差不多是现烧现买,不愿意买多了烧不完再搬回去第二天晚上再搬来。煤球销售不好,五富拿眼留神左右摊上有什么破烂,他去收拾那些酒瓶子和塑料饭盒,摊主不给他酒瓶子,只给塑料饭盒,而且要他打扫饭桌。五富很殷勤,塑料盒收了不少。
我们每每是半夜一两点才能回到池头村,几天下来人就疲惫得支持不祝五富能走着路就瞌睡,我不行,他就让我拿个棍,他握一头,我握一头,我在前边走他在后边瞌睡,他瞌睡还起鼾声。夜里街上人少,但车开得都猛,每有车过来,我一停他就醒了,问:还没到?我说:你能睡着?他说:我刚才做了个梦,正吃……他又闭了眼瞌睡了,人瞌睡了五官特别丑恶,我就像拉着一个走尸。
煤球王见我们太累,允许了我们夜里不回池头村就睡在他的棚里,但五富的鼾声像拉风箱,甚至一会儿急促,一会儿却停止了,突然又噗的一声,吓得我们以为他憋住了气要过去了。我神经有些衰弱,煤球王更是难以入睡,先是用棉絮塞耳朵,后来五富鼾声一响他便用顺手的东西去掷,一掷不响了,不掷又响了。天明后五富的身上尽是臭鞋烂袜子和枕头,以及我们所有的衣服。煤球王坚决不让五富睡在他那儿了,五富便每天晚上回池头村。我们说好,第二天早上收购站门口见,而我则是每早上煤球王送煤的时候,让我坐了他的运货车到兴隆街。
一个晚上,我拉了一车煤去夜市,路过一家宾馆,宾馆的一个人让我给他们送一车煤,我送去了,收煤人说出纳下班了明日来结账吧。这是我次卖出了整车煤,就买了一条鱼早早回棚屋炖起来,我要让煤球王看看我的手艺。他回来了,带了一只狗。
他说:今日运气好,尽捡东西。
我说:我运气比你好,卖了一车煤。
他说:你就会吹!
我说:不卖一车煤,我能买了鱼给你?
他从怀里掏出个小坤包,说:你给我买鱼,我送你个包!
街上经常发生抢包事件,我就怀疑他了,像他这德行,容易是坏人。
包儿哪儿来的?
捡的。
该不会是抢的吧?!
你啰嗦得很!
我一下子脸色变了,我有责任管教他,我是他叔。我说:你看着我!
他看着我。
抢的?
捡的!
他比五富强硬。
抢的!
我抢的我还不把包里的东西拿了而把包扔了?
他从锅里把鱼用铲子截了一半,却夹给了拴在门口的狗。
咱还没吃哩你就喂狗?
我就喂了,咋?
他虎着眼,又从锅里夹那半条鱼,我过去拦他,他用力筛我,锅就撞翻了。他抓起包就要从院墙里扔出去。我把包又夺过来。他向我吼:哇哇哇哇哇哇哇!
我笑了,他发火就证明了他的清白,他要是不发火我倒要连夜离开这里,我不愿意和一个抢匪住在一起。我说:咱刘家世世代代没出个贼呀匪的,这包是你捡的?
他说:你要不是我叔,我得揍你!
我说:别以为你叔不如你,论城市生活你还嫩哩!我告诉你,别人抢了包,掏了东西把包扔了,你不要捡,现在抢包的多,你捡了空包别人以为你是抢匪!包里还有啥?
他说:有啥?!一卷手纸,一个小镜子。
我把包儿揭底儿倒,倒出来的也只是一卷手纸一个小镜子,但又掉下来一条项链。项链是用一个小纸包包的。他一把拿过了项链。咦,这玩意儿可以卖几百元吧。
我说:良子,这可是我发现的,最少卖了钱一人一半。
他扔给我五十元,竟然用很鄙视的眼光看一个长辈。
我拿了五十元又去街上重新买鱼,继续做炖鱼。这一顿我们都吃得肚子胀,睡下了,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煤球王却拿了钱在被窝里数。他到底有多少钱?只听着刷啦刷啦响。我说要数出来数,被窝里有我的屁哩。他不理我。
我说:你一天能收入多少?
他说:睡你的觉,好不好?!
夜渐渐地深了,门口的狗却不停地叫,叫得真烦。煤球王爬起来把狗放在棚里,狗就在我们被单上跑,又卧在我枕头边,我气得给了它一掌,它又跑到煤球王那头,后来我就睡着了。
这只狗自此成了煤球王的宠物,他每天都给狗买东西吃。我半夜回来冰锅冷灶,狗盆里却总是鱼和排骨,我当然教育他了:咱是来干啥的,能也要会攒钱,你将来花钱的地方多着哩。他给我翻白眼。我实在不愿在这里呆下去了,但我得尽快多多,我忍了。
可我已经第三次去那个宾馆要煤钱了,还是没要来,先是宾馆人说谁买的你找谁去,我只记得买煤的人五十多岁,头发灰白,他们问了头发灰白的人后出来说有这回事,但现在没钱过几天来,而我过几天再去,门卫死活不让进,我在门口吵,大堂经理就招呼保安:轰出去!我便被轰出来了。
煤球王说:是不是需要我去?
我说:去打架呀?保安一大帮,你打得过谁?
他说:我不打他们我打我自己,用刀片子在我额上划,划个血头羊行吧?
他的额头是有两道白印,当然是治愈得非常好的疤痕。我说:你划过?
他说:市容收过我的车子要罚五百元,我急了,拿刀片在额上划,他们就退了车子,款也不罚了,一个人还说这小子狠,到咱市容队当个补外队员吧,我没去。
他这么说着,我就更不敢让他帮我讨债了,当我再一次被宾馆保安轰出来的那个晚上,我准备好了,要告诉他:煤钱是讨回到了。但他竟然一个晚上都没回来。
煤球王是不会走失和吃亏的,这一点他比五富强,我担心的是他开运货车出事或者与人打架。夜里两点多,我去找煤场门卫,这么晚了煤球王怎么没回来?门卫说你看看运货车在没?我去停车场看了看,那辆红色的三轮摩托运货车在。门卫说你看看西服领带在没?我回棚里才发觉西服领带不见了。门卫说:这就不用管了,只有别人吃亏,你侄儿吃不了亏。
这是什么意思?我回坐在棚里等,他还是没有回来,我就睡了。这一晚上的蚊子非常咬,好像全煤场的蚊子都跑来了。煤场的蚊子都是黑的。我睡不着,就想孟夷纯。蚊子也是咬得孟夷纯睡不着吗?睡不着的孟夷纯在数着筹到的钱吗?数着数着会不会想到我呢?在问:好久怎么没见他了?还是脑子里一想到我立即便念头闪过了,就像是玻璃桌上的水,手一抹就什么也没有了?
咬孟夷纯的蚊子能飞来咬我多好。
第四十九章
第二天早晨,我走的时候煤球王还是没回来,而我又比五富提前到了收购站。五富的衣服脏得看不出个颜色,我训斥他:你少睡一会儿也该把衣服洗一把水么,穿着不难受?他说:不难受。我说:你不难受,别人看着难受哩!他说:白天拾破烂晚上卖煤能干净?我说:厕所里的蛆还白白的哩!我说我本来要带他去见见孟夷纯的,现在不带他去了。五富没有生气,说:难怪你穿得干净!却从怀里掏出了三百五十元,说是杏胡让把大家捐的款转交给我。我已经出来这么些日子了,杏胡还是依旧收缴捐款,这让我感动得眼睛都红了。
我有了一种幸福感。人的运气从大清早的情绪而定的,今天的情绪好,运气可能就来了。可不,离开收购站,我一到十道巷就收一麻袋的空易拉罐,这是从未有过的事,而且在八道巷又有人把装修剩下的旧钢窗旧防盗网卖给我,还在那个豪华宾馆门前报栏又碰上了那些老头,他们依然在看楼练颈椎,却每人都提了一大包旧报纸在等我。三轮车上破烂垒得高高的,我希望有人能看见,可茶馆门口的收停车费的老头没在那儿蹴着,宾馆的保安也不在门口,小酒馆的门还关着,所有的熟人都没有。我就蹬着车子慢慢地走,不急于去收购站,走过了九道巷,再折头走十道巷,我游行哩。
十道巷的拐弯处,前面有个老头提着鸟笼,老头回头看了我一眼,又把头拧过去继续走他的路。这死老头!但鸟笼里的鹩哥却叫了一声:刘高兴!
这老头每天要遛鸟的,他有时热情地叫我刘高兴,有时见了却冷若冰霜,而鹩哥也认得了我,鹩哥始终如一问候的。我说:你好!
鹩哥说:你好!
我说:唱个歌,唱个歌!
鹩哥说:吹箫!吹箫!
鹩哥比老头知道我的心思,我就取了箫来吹。我吹的是:东山坡呀西山坡,山山坡坡唱山歌……老头却提着鸟笼不停点地走了。老头今天心情不好,不好你就不好着吧,我还要继续吹箫。从头来,吹:东山坡呀西山坡,山山坡坡唱山歌,唱得山歌落满坡,幸福生活……
吹着吹着,不吹了,哇,你知道我看见谁了,我看见了孟夷纯,孟夷纯在路对面向我招手哩。
啊,孟夷纯还能向我招手么?!
如果在大街上碰见了孟夷纯,孟夷纯还在恨我,看见了我而不理我,那我会伤心地哭哩,可孟夷纯在给我招手了,态度还是活腾腾的一朵花,我就胆正了,蹬着三轮车横穿马路,行驶的汽车因此停下来了十几辆。
我们是站在了那个垃圾桶前见的面。
她说:不错么,今日这么多收获!
但我站在她的面前,有些窘。因为一切来得太突然,我的头发乱着,蹬三轮车时把裤管挽了起来,又挽得一个裤管长一个裤管短。我怕我身上汗味重,所以站在垃圾桶前。
孟夷纯似乎全然没在乎这些,她脸色红扑扑的,说:我还以为你生了我的气,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说:你那天那么凶的。
她说:我那天凶吗?女人就是过几天脾气好,过几天脾气不好。也怪我不好。
我说:是我不好。
她说:我一凶那你也就不再来了?
我说:我怕你不见我么。
我想不来我能说这句话,而且声调扭捏,像是撒娇。若是听见这话是别人说,我牙根都发酸发麻了,这哪是我的风格呢,可我偏偏说出了这句话。我的脸刷地烧了。
又害羞了,又害羞了。孟夷纯又用指头来戳我额,手过来了却拍打了我肩上的土。
还能有什么让我心里舒坦吗?刘高兴毕竟是不懂女人的,女人对你好起来这么好,对你凶起来却那样凶。但我现在得装出很男人的气概了,我扬了头,说今天凉快,又说今天运气不错,再说:你这一身衣服好看得很么!
她说:是衣服好看还是人好看?
我说:人好看。
她说:人好看了你就多看几眼!
我说:我不多看,那边店铺有人往这边瞅哩,我这样子和你在一起辱没了你,你先走,我交了破烂后去店里找你。
她说。我不!
现在是轮到她在撒娇了。
我们就相厮着一起去收购站。那天的街上如果人再多点,肯定要发生交通堵塞了,一个漂亮时尚的女人和一个灰头土脑的拾破烂的说说笑笑并肩行走,身边过往的人都拿异样的目光看我们。我瞄着了一个人噢了一声后鼻子突然流血,流吧流吧,所有人都流鼻血去吧!
我说:这些日子没见,你胖了?
她说:真不会说话,现在兴见了女的要说瘦的!
我说:你真的胖了,胖得更好看!
她说:是不是?可能是有了好事的缘故吧。
我说:案子破了?
她摇摇头,告诉说她又筹到了五千元钱给公安局汇去了,而让她高兴的是韦达终于同意让我和五富一起去公司干活,也不是干门卫,而且她从韦达他们那里收集了一大包旧衣服,这些衣服都是好衣服,只是样式有些过时。
我说:真谢谢你!
她说:跟啥人学啥人,我这也是拾破烂吗?
我说:我请你吃饭!
在收购站交货的时候,瘦猴不停地偷看孟夷纯,我拿脚踢他的屁股,他说那是谁?我说朋友。他说你有这样个朋友你就不叫刘高兴了。我说就是有这样的朋友我才叫刘高兴的。他说行呀,商州炒面客到西安也能挂拉上洋马子了!
在一家小川菜饭馆,我们吃到了最丰盛的一顿饭,两个素菜,两个荤菜,还有一个鸡蛋西红柿汤。当然是我埋的单。吃完饭,我们到美容美发店,她果然取出了一个大包裹,里面全是一些西服西裤衬衣衬裤,还有鞋,都是皮鞋。孟夷纯说上楼去你穿着试一试,我不愿意上楼,孟夷纯脸上掠过一丝难堪,没说二话,拉我便到曾经去过的茶馆里,要了一个房间,一关门,一件件拿了衣服让我穿。最后选定了一件衬衣还有一件西服,又给我系上了领带,推我到镜子面前照。她说:没想你还是个衣服架子,哦,像个老板!我嫌领带系着憋气,把领带拉掉了,又要脱下西服,她从后边就抱住了我,我立即挣扎着要反过身来,她说:我是抱衣服的,你别胡想呀!我仍是反过身来搂住了她,她说:我家亲戚来了。我并不知道她家亲戚来了是什么意思,还说:谁来了?手就到处乱摸,摸出了一手的血,她说: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我原本并没有想要这样的,是她一挑逗,我就把自己定下的规矩全忘了。她说脏,我说我不嫌脏,她说这样要生病的,我说我不怕生病,她说你不怕生病我还怕生病呢。我就老实了。她却安慰我,几时到池头村去好好给你,可你不能让我受垫噢,我说我一定要买个沙发床垫的。服务员敲门来给茶壶续水,我们就分开椅子正正经经坐了说话。
我说:你怎么给韦达说的,他就能同意我和五富去公司?
她说:具体怎么说的你不用管,反正他同意了。
我说:他同意了,我倒还不愿意天天就见到他。
她说:为啥?
我说:……
聪明的孟夷纯当然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她是闷了一会儿,最后还是说:你和五富去了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辛苦么。我弯过身去抓住了她的手,说:夷纯,夷纯!她说:你不要说了,咱不说这些了,今日高兴,咱说说别的吧。
可我们一时又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我在口袋里掏纸烟,手碰到了五富交给我的三百五十元钱。孟夷纯说:也给我吸一根。我把纸烟盒递给她的时候,也递给了三百五十元,再递给她打火机的时候,也递给了我身上的一卷钱,我没有数,可能有二百元。
她说:还给我钱?我已经给公安局汇去了五千。
我说:那五千能够吗?
她坚决不拿。我再一次把钱塞到她的口袋,说:不就是一点钱么,你不肯拿就把它扔了去!
她说:瞧你张狂的,是不是这些天收入好了?
我没敢再说杏胡他们捐款的事,只告诉我在煤球王那里加班卖煤了。
她说:卖煤比拾破烂强么。
也不强,我就给她讲煤球王的故事,给她讲煤场里的见闻,给她讲宾馆如何赖着账不给,孟夷纯眼睛就睁大了,立即拿手机给韦达拨电话,韦达回应说他认识宾馆经理,他要给经理通融一下,宾馆不敢不付钱的。她放下手机说:你明天就去要账,就说是韦达让你去的!我点着头,但我对于韦达的能力半信半疑。
我就是穿着一身西装回到了煤场,煤球王还是没有在,门卫说良子是半早晨回来了,睡了一会儿又出去送煤了。棚屋的门没有锁,其实棚屋压根就没有锁子,只是门环上插了一个木棍儿。那只狗拴在床腿上,把床单抓到了地上,而且在上边撒了尿,我把狗拉出去拴在棚外的树上,开始和面要搓麻食。以往搓麻食都是在案板上搓,这天我情绪好,洗了那个草帽在草帽上搓,搓出的麻食是卷状,又有花纹。一直搓到煤球王回来了,我又装大起来,说:昨晚你浪到哪儿去了?!
他说:你会不会文明说话?喝酒啦!
我说:喝酒能喝一晚上?喝酒还拿了那个包儿和项链?!
他说:我爱拿不拿的你管得着?
他走出了棚屋,却突然问:狗呢,狗在哪儿?
我说:不是在树上拴着吗?
他说:在哪儿?!
我走出来,树底下果然没了狗。他在煤场里大声叫:丽丽,丽丽!竟给狗起了这么个名字!但丽丽没有出来。煤球王冲进棚屋发火:谁叫你把狗拴出去的,咹,狗碍你啥事了你拴出去?
我说:丢就丢了,给我凶?你叔不如一条狗?!
他一下子跳起来,把手里的手机摔了。
我怎么受得了他这样,这不是恨嫌我吗,我刘高兴是不吃下眼食的,何况还是我的侄儿!我顺门就走,他说:脱下我的西服!我说:你拿眼再看看,是你的西服还是我的西服?
一走出煤场,我觉得大人不见小人怪么,可我已经走出煤场,回头看看,煤球王也并没有撵我,那我就走了。
第五十章
在池头村里,我把那些衣物分给了五富、黄八和种猪。
我们四个男人,从此都穿着名牌西服,这在池头村所有的拾破烂人中,我们是独特的。村人见了我们叫:西服破烂。
有人以此怀疑起我们的身份:能穿这么好的西服拾破烂吗?街道办事处的人就曾查询,以为我们一群对社会不满而故意拉着蹬着装破烂的三轮车架子车上街,如今上访的人多,我们是不是其中的。我们百般解释了,架子车和三轮车是归还了,可又嘀咕我们的衣服是偷窃的。
五富他们就不愿意再穿西服了。唉,沐猴戴不了王冠,穷命苦身子,那我也没办法了。我依然是名牌装束,去村口市场上吃麻辣米线,瞧着韩大宝对面走过来,我故意直直走过去,他竟然身子侧了一下给我让道,已经让过身了,才发现是我,一把扯住说:咋是你?
我说:是我呀!
他说:有了这身行头?
我说:不就是一身衣服么。
他说:瞧这口气!混得比我还像城里人了!
我说:我去找过你几次都没找着。
他说:得是来感谢我呀?
我说:当然感谢,也给你说个事。
他说:噢,还得寻我么!
我就说了,我们在兴隆街那儿很安分,没惹出个什么事儿给你脸上抹黑,也很勤快,收入还过得去。但是,地盘毕竟还有些小,能不能再给我们几条街巷?
我说这些话时心身特别的放松,甚至有些小得意,言辞出奇的顺溜,但我立即意识到坏了,怎么能对韩大宝嬉皮笑脸地说话呢,他是领袖,他是破烂王啊!果然韩大宝乜视着我,说行么行么,脚步却没有停就走过去了。
我应该说一句请他一块吃麻辣米线的话,我没有说,这更是我的错。回来给五富提说了这事,五富说人家缺那一口呀?!而我心里总是不安。
人有一事不妥,后来必受此事之累,这如同碗盆一旦有了隙缝,肯定将来就要漏水,我果然得罪了韩大宝。他不但未为我们扩大地盘,而兴隆街又出现了两个拾破烂的人。这两个人蓬头垢面,怯怯弱弱,一看就是才从乡下来的,本来我们应该亲切他们,可一个萝卜怎么能两头切呢,我们就凶起来,轰撵他们。他们虽不敢和我们打架,却就是不走,说是韩大宝安置他们来的。事情就是这样的糟糕,五富开始埋怨我,我向黄八和杏胡夫妇请主意,黄八就破口大骂,骂现在当官的口口声声是公仆,为人民服务哩,可有一点权就要用手中的权为自己谋利哩!我说你胡骂啥呀,韩大宝是官吗,他不是官!黄八说那咱就轰撵,用武力,我帮你们用武力!杏胡说你又给刘高兴惹麻烦呀,你给刘高兴惹的麻烦还少?!杏胡的分析是如果不是韩大宝安置的,那一轰撵就跑的,既然轰撵不走,那就真是韩大宝安置的,如果是韩大宝安置的,你们怎能轰撵得了?只能去找韩大宝。
五富便反复地催促我去找韩大宝,唠叨得像个妇道人家。何必呢,五富,没有屠户咱还能吃连毛猪?我没有去,拿了箫来吹。
五富说:你不去?
我说:为啥我去?
五富说:你屙的你擦!
他觉得没说好,又说:你是。
承认我是,那我错了也是应该错的,清风镇有句俗话,掌柜的打了瓮,片片都能用,大的苫墙头,小的塞墙缝!我问五富知道不知道这俗语,五富苦愁个猪脸进屋睡了。
我还是吹我的箫。其实我心里有底,就是:一旦拾破烂彻底无望,我们就可以无牵无挂地去韦达公司干活了。去韦达公司的事我之所以没有给五富说,也没给黄八杏胡他们说,是觉得毕竟韦达并不情愿见我,我也不想见着他而勾起对他和孟夷纯关系的不快,再是丢了拾破烂有些可惜,何况还舍不得离开黄八和杏胡夫妇。现在韩大宝一排挤,倒造就我们华山一条路地去韦达公司了。
可怜的五富,他不知道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晚饭也没有吃,一觉睡到第二天,脸浮肿,嘴角起了火泡。我们再次去了兴隆街,街上人说:现在拾破烂的咋这么多!五富就问是不是还看见了两个拾破烂的,一个冬瓜脸,一个粗脖子?那人说:是呀!五富就呼哧呼哧出粗气,从路边拿了一块砖放在架子车上。
我说:你别胡来呀!
他说:不打,咱喝风屙屁呀?
我说:要打你打,我可不出手。
他说:不用你打。我打赢了你请我喝酒,喝白酒,打输了,你给我买创可贴。
瞧他傻样!放下三轮车,我钻进一家家具店了。
这是我第五次进家具店。这家家具店的老板长得面善,我和他讨价还价,终于将一张床垫由五百元降到四百元,五富就进来了。我说五富快来看看这床垫,五富一手的油黑,他不敢摸,说:这么好的床!城里人会享福,睡这号床做梦怕都是带彩儿的。我就向他借钱,我只有三百五十元,借五十。五富说你给谁买呀?我说我给我买的,买下了你可以来坐一下。五富嘴张开,拿手在我脸前晃。我说你干啥么?五富说你得是生病啦?咱拾破烂的睡沙发床?老板就训了五富,说:你们是拾破烂的来戏弄我呀?五富说:谁戏弄你了?脖子梗得老长。老板说:你是来闹事的?!我把五富拨开,说:不会说话就不要说,掏五十元!五富说:不掏!我再说:掏不掏?五富说:不掏!
我不能在老板面前丢了人,举了手就要扇五富,五富像牛一样扑过来,抱住了我的腰,竟抱着出了店门。
我生五富的气,但也正是五富这么抱了我出了店门,我才不至于在老板面前再尴尬。五富抱着我还不松手,我就笑了,说:不买就不买了,你见着他们了?
五富说:人没见着,狗日的怕是瞭见我就藏起来了,架子车在路边,我把气门嘴给拔了!
到了这步田地,我又得护着五富了。我嘴上说打起来我不出手,可五富这憨头拔了人家气门嘴,人家真要撵来打他,我能扔下他不管吗?我往四周看了看,没有出现那两个拾破烂的,我说:快走!五富跑得比我欢。
那天,我们基本上没有收到什么破烂,五富急躁得像一头发情的母猪,不安静,又嘟嘟囔囔。我得宽宽他的心了,靠在路灯杆上,我说:天上掉下来个肉夹馍吧!五富竟就往天上看。天上一道一道红云,像犁过的稻田,而路灯杆上忽然有个石头落下来,吓了我们一跳,忙看时才是一只麻雀,小酒盅般的一只麻雀,倏忽又飞走了。
我说:不急五富,好事就会来的,你要信我。
五富说:信你。
但是,孟夷纯几天里没有来通知我们去韦达公司的事。我设想的情景是:买了沙发床垫后,孟夷纯在某一个上午或黄昏从城里来到池头村送通知,她就可以舒服地躺在我的床上了。而床垫没有买成,孟夷纯又迟迟不来通知,这其中是不是有了什么神秘的因果关系?又等了一天,孟夷纯依然没有来,我也就急了,终于到美容美发店去问她个究竟,谁能想到呀,巨大的灾难就降临了。
那是十三号,十三这个数字真的是凶数。
那天我离开池头村去美容美发店的时候天在阴着,手伸出来有些凉。夏天似乎就要过去了,立秋后晚上再没能什么也不盖地睡觉了,而且瓜果吃了容易闹肚子。我临走叮咛五富把夹克穿上,又将窗台上的那碗兰草移放在了墙根,因为窗缝老往里钻风。兰草经过一个夏季,养得还好,但天刚一转凉,叶子就黄蔫了,五富几次说扔了算了,我没有舍得,那个早上我还给兰草说:一定要精精神神活,活到我买了床垫,让孟夷纯能看到你!我这么给兰草说话,咚的一声,墙上的木架板就掉了下来,孟夷纯穿过的那双鞋,一只落在了地上,一只落在了墙根的兰草碗里,鞋湿了,兰草碗也翻了。这都是预兆,不祥的预兆!但我是那样的笨,当时竟然就没有想到这是预兆。
孟夷纯被警察抓走了,并且被抓走了五天。
站在美容美发店对面的那堵墙下,墙上是我来见孟夷纯时所划下的二十多条道痕,孟夷纯却再不见了。我是知道的,孟夷纯从事的那份工作最容易出事,可西安城这么大,从事和她一样工作的人不计其数吧,天上的鸟儿拉屎,偏不偏就落在她的头上?
美容美发店那个胖乎乎的女店员,她是和孟夷纯关系最友好的,她告诉了我,这一条巷里的美容美发店向来都是十分安全的,因为兴隆街派出所所长的两个亲戚也在这里开了店,而每个店的老板都与所里的一些人熟,并定期带着礼去看望他们。但是,偏偏北京的一位负责全国扫黄打非的大官来到了西安,市公安局突击整顿一些舞厅、洗浴中心、美容美发店,而且是专门一批警察,根本不给各派出所打招呼,突然行动,孟夷纯就倒霉地撞在了枪口上。那天六七个警察进来,吓唬着在楼下的所有人都靠墙站,不许动,老板假装着要去那柜台上取纸烟,她就想按柜台下的电钮,那个电钮一按,楼上的人就会知道有紧急事情能立即隐藏起来的,但警察并没有让老板走动,而三个警察就冲上了楼,把孟夷纯和一个客人带下来了。带下来时孟夷纯是没有反抗,也没有哭,往门口停着的一辆警车上走,老板是拿了一条毛巾往她头上一盖,但孟夷纯是把毛巾取了,她嫌弄乱了她的头发,还回头朝大玻璃镜上照了一下。
胖女子说:这条巷道那天抓走了二十八对,我们店就孟夷纯和那个客人,后来老板也被抓走了。
我说:最该抓的就是老板!
胖女子说:老板已经放回来了。
我说:她怎么放回来了?!
胖女子说:听说那个大官回京了,她有关系,疏通后就回来了。
我立即去找老板,这个平日总在脸上涂一层厚粉的女人,脸上已没了颜色,粗糙而松弛着皮肉是那样的难看。我问孟夷纯现在在哪儿?她说在劳教所里还能在哪儿?!她对我一直态度刁横,我只好软下口气,央求她也疏通疏通关系把孟夷纯放回来。她说她是带着人去疏通过,回话是罚交五千元就可以放人的,你有五千元吗?我哪儿有五千元呀,今辈子手里没有一次性经过五千元。我说孟夷纯是你的店员,也是你的摇钱树,你应该赎她呀!她说你是她的乡党你赎呀!我说我没钱么。她说我也没钱。她坐在那里吃纸烟,吸一口吐一口,还把烟雾往我脸上喷,我真想给她一拳头,但我忍了,不停地求她,几乎什么话都说了,比如,如果赎了孟夷纯出来,孟夷纯绝对会再赚钱还你;比如,我和孟夷纯今生都记你的恩德,来世也给你做牛做马;比如,你要觉得这些许愿都是虚的,我从现在起就来店里干活,洗床单,烧炉子,冲厕所,我把你叫姨。她说你要给我五千元,我把你叫爷!她拿了拖把拖地,拖地是启发着我走的,我就抹着眼泪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