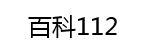草
作者 |阿树
一
草长在塄上,坎上,坡上、庄稼地甚至石头缝里。无论在哪里,都能看到它们身影。它们总有无穷尽的力气,蓬蓬勃勃,似乎在所有的日子都走在生机存续的路上。即使冬天,在积雪下的土层里,它们也是以另一种方式悄悄生长。
有些村里人不信:那一坡坡的草一到冬天就被霜打的蔫头耷脑,一点小小的火星就能把它们烧成灰烬。——在他们的意识里,草的生长只是是春天和夏天的事。
海爷爷见不得这些只看表象的人,就惩罚他们抡起六七斤重的老镢头,挖房后被雪花盖住的一大片荒地。只一会功夫,他们身后,就有了一片吐着热气的新土和一堆象牙白的茅草根。海爷爷指着那蓬白白胖胖,像箭一样在土层里穿行的茅草根说 : 你们看,草在冬天也不曾歇着。它们是真正的潜伏者,它们看起来叶茎枯萎,而根芽却在土层里悄悄生长。
二
草把本来连接在一起的陆地分割成各种图案。把它们分割成庄稼、树林、房屋、沙漠和水域的版图。它们还用繁荣和荒芜,把整个世界分成村子、闹市和街区。当然,更多的时候,它们喜欢用人口的密度和房子的高度来划分。虽然名义上分了,但它们一直不会死心,但凡只要有丁点儿的机会,它们就会攻城掠地,迅速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因为很早以前,大地基本上全是它的地盘!
看看西安明城墙的砖缝,山城重庆石板路与石板之间的缝隙,你就会明白草是个“大野心家”,它是多么想一统这个世界啊!
三
吾乡没有思想家,没有人能弄懂草的思想。它只要长在庄稼地里,吾乡人就会不择手段把它们弄死,甚至连它们刚露出头的嫩芽也不放过。从古至今,只有庄稼人对草的感情是最复杂的。恨时就拿起锄头,“锄禾日当午”,即使“汗滴禾下土”也要灭了它们。“锄禾”——说白了就是疏松土壤,顺便把草给灭了。
四
鸟在草丛里垒窝、繁衍、生息,人类也把房子盖在草肆意生长的地方。那时,草们的悲伤就像流动的河水,满世界都是它们的尸体。不远处,草尖上挂着露珠,那其实是活着的草流出的眼泪。更是它们呼唤同伴的风铃!
有风从断裂的土墙那边吹过来一些慨叹: 墙倒了,老屋垮了,草又深了!
“八月秋高风怒号,
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
高者挂罥长林梢,
下者飘转沉塘坳”
说的是某个黄昏,风刮翻了唐人杜甫老汉的茅草庵,把草吹到河对岸去了。老汉怼天怼地怼人怼社会,可是他唯独没有怼草!因为草与他有恩,在没有大厦可居的情况下,是草庵容下了他的肉体和灵魂。
吾村人海爷爷家的草庵被大风刮倒后,他骂风,骂风是熊货,说它有本事咋不把那些高楼大厦也吹翻。捡桃捏pa,净欺负日子不好过的人。
海爷爷还说:这世上大慨就没有不长草的地方,如果有的话怕只有石头上生不出草。如果石头上能长出草,那石头一定是被草给捂热了。
五
地上的草,有叫树的有叫花的,海里的草有叫珊瑚、海带的。长在河里湖里的草,叫水草。徐志摩说: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云彩在天上,水草在他身后康桥的湖水里。只是总有人说他那时候心情不好,节奏被情绪带偏了。
吾乡人多用茅草鸭草蓑草盖顶。沟沟壑壑的地里,看庄稼的庵子是草盖的顶。早些年,买不起瓦的人家,他们小偏厦的屋顶甚至是大房的屋顶,也是用只要力气不要钱的草盖的顶。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行走在新疆、甘肃一带,看到那地方的人们把一片一片比人还高的苇草割倒,用马车拉回来,摊放在屋顶上,上面再抹一层黄泥。这样做成的房顶据说不怕风吹日晒,甚至雨淋也不怕。
六
细细想想粮食,也是草籽和草的根茎。这世上哪一天如果没有了草的影子了,估计人类也就离灭亡不远了。华夏民族是智慧的民族,很久很久以前,就知道拔草治病,先有神龙氏尝遍百草,后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父亲常常说起年轻时,他和海爷爷去秦岭的太白山里拔草药。那浩瀚的大山里,草全是宝贝。某些草的基因是人体内魔障的克星和天敌。由于大秦岭的草药花样繁多,几乎是个天然的药草宝库。所以,世上就有秦岭山里无闲草的说法。
这个星球上总有一些民族自我感觉良好,认为他们的品种是多么多么的优秀。但他们不知道或者多少知道一些,那就是只有聪明的中国人知道把一些草的枝、叶、根茎,按照不同的配比拿来熬成汤汁,或捣碎敷在患处百病。这些草的密码似乎一直就藏在中国先辈人的智慧里,什么金钱草、石斛、灵芝,雪莲、人参,既是草又是药!
七
草不但有野心,还特“小强”。急功近利的现代人,恨庄稼地里长草,就造出了各种狼性的毒药。可是草的生命力依然无比强劲,表面是这一季屈服了,可下一季它们又从地里露出头来。没有听说过用什么人造的毒药能强大到把草根除,甚至野火也无可奈何!草真的比“小强”还“小强”!或许有人想到过以草治草,就像晚清的“以夷克夷”一样。如果真的这样,不知道草们会不会惊慌失措?
假如真的某一天,地球上的草被人类收拾干净了,那人类的寂寞绝对会成倍衍生。
我无法想像,天地间没有的草覆盖会是什么样子,最起码鸟类会减少很多。没有了草籽和藏身在草丛里的昆虫,鸟会飞到别的星球上去寻找出路吗?估计这是一个让地球人头痛的问题。
没有了草,茂盛的大草原上就剩下荒凉和死亡,没有马头琴,没有蒙古包,没有毡房,也就没有了爱情。成群的马群羊群不见了,草原腐烂成了一片一片死海。再也不会生出“西西里海的情歌”这样让人心醉的旋律。
八
春天一过,村子东头的坡上和远处的甸子里,草最爱捉弄风。风来了,草就顺势倒下去。风哈哈大笑,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草干爬下了。其实,草是不屑和风这样的疯子一般见识。风没有耐力也没有眼力,那一日吹倒了草垛,把在草垛里面热火朝天恩爱的哑巴和男人死人五六年的桃花嫂吹了出来。桃花的公公叫了本家的一帮人,用绳子牵着二婶游村,二婶无脸,跳了井。
从此,村子很多人都恨风,骂风。其实风该骂,草垛也该骂,不是它们,桃花好好的,天天磨魔芋豆腐卖。魔芋也是草的根茎,加上碱和酸,经过几道工序,它就成了美食。草成就了桃花又算计了桃花婶的性命。
九
吾乡在大秦岭南坡,山野里到处是草。经过一个春天和夏天,草就像成熟的女子,被风撩开衣襟诱惑亮着银光的刀锋。
前些年,家家户户喂牛种地,庄户人家是真真的耕种世家。一到割青晒青时节,青壮男女专寻青草茂盛的地方弯腰开镰。“割,割,割”,他们“呸,呸”往手吐上口水,顿时银镰翻飞,“嚓嚓”声响起一片。在阳光和风声里,似乎有万千双手摇着旗帜朝他们嘶喊。汗水从皮肤的毛细血管往外溢,他们顾不上抹一把,他们要把这塄塄坎坎沟沟上的草放倒。
晒干后一流的草喂牛,二流的草垫圈。好草喂好牛,好肥种好田。丰收和富裕,有人的功劳牛的功劳,也有草的功劳。
自从大部分精明能干的年轻人和中年人都进城后。村子里留下了一些老屋,老屋的门上挂着生了锈的铁锁,窗子里再也看不到有阳光把明媚分一些进去!欢声笑语像干枯了溪水的河流,浣衣的清秀女子把她们的木棒槌丢进河里。只一个转身,草就起来了。草的绿浪不顾一切地淹没了她们的棒槌和欢声笑语。
大部分人想到故乡,首先会想到院子疯狂的草,路边疯狂的草,庄稼地里疯狂的草!
他们思念故乡,可他们怕草,草已经盖住了埋着先人的黄土堆。他们一阵阵脊背发凉,怕他们死后,埋他们的土堆也很快会被一蓬一蓬的草吞没!
房子倒了,它们和炊烟一样被草按倒在身下……
极少的几个留守老人,从草们没来及遮住的光阴里蹒跚到路口,望着城里的灯火。那里有他们的儿孙,城市里的草比乡下的草少,他们不想被草按倒,他们想去没草的地方。可是,他们怕没草的地方无论如何都不收留他们……于是他们只能看着太阳由东照到西,日子由白过到黑,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和草搏斗,只能任草疯狂,任它们长满院子,爬上窗棂上,钻进门缝里。再不久,他们会一个个倒下,最终变成草丛的肥料!
哎,茂盛的村子里的草哟……
—END—
【专栏作家】阿树,本名杨昕,在报刊和网络媒体发表有散文、小说作品等,现居西安市。
来源:读书村,版权属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