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
奥登说:“对于批评家,唯一明智的做法是,对他认定的低劣作品保持沉默,与此同时,热情地宣扬他坚信的优秀作品,尤其当这些作品被公众忽视或低估的时候。”我也同意,对那些平庸作品可以忽视,但有时那些作品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批评家吹捧起来,这时我们就不能坐视了。我们会感到那是对我们智力的冒犯,感到我们的判断力被侮辱,就像有人当面嘲笑我们是傻瓜一样。没错,那些批评家的奉承不是在作者的家宴上,而是在公众媒体上说的,那就是当面在嘲笑我们。
奥登曾说:“要提高一个人对食物的品味,你不必指出他业已习惯的食物是多么令人作呕——比如汤水太多、煮过头的白菜,而只需说服他品尝一碟烹制精美的菜肴。”在许多普及教育和传播文化的场合也是如此,只要提供一种更宜人的对象让人尝试、选择就可以了,不需要更不应该去批评甚至取消别人习以为常的宗教、风俗、习惯,那只会招致反感、对立和抵触。很多以文化或文明优越自居的人都不懂得这一点,所以往往以失败告终。
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逝水年华》,直译是《追寻失去的时间》,但作者如果知道中文这样译,一定会深受感动。因为抽象的时间概念被冠以有出典的逝水意象——孔子:“逝者如斯夫。”生命的流逝被具象化了;同时,“年华”本身就是个由比喻性意象(华=花)固定下来的名词,“逝水年华”的诗性意味较之“失去的时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就是汉语的象喻式表达特有的美感。
古典音乐界的本真演奏,曾经很流行过一些年,近时已趋于沉寂。理由很简单,本真演奏所使用的乐器,相比今天的乐器来,表现力终究是要逊色的。如果没有表现力的提升,二百年来的乐器改进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我还是很喜欢听本真录音,觉得可以了解作曲家想制造什么样的音乐效果。如果莫扎特、贝多芬的时代已有现代乐器,他们写出来的音乐一定不同于现存作品的。这就是本真演奏的意义所在。
巴洛克时代的音乐家,作品数量都比现代音乐家为丰富,巴赫的数量已经够多的了,但维瓦尔第和泰莱曼还要更胜一筹。我听泰莱曼的唱片不多,主要是一些协奏曲和奏鸣曲。窃以为,认识一个音乐家的伟大和深刻,有时通过独奏作品最为便捷。相信没有人会否定巴赫六首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和《帕提塔》以及六首大提琴奏鸣曲的伟大,这些独奏作品展现的巴赫有时比他那些宏大的管风琴曲更丰富、博大和精邃。
在音乐爱好者的微信群里聊天,惊讶地发现彼此对乐器表现力的看法有很大出入。按我的理解,表现力是一个指称乐器再现音乐作品的综合能力的概念。其中音程的覆盖面、音色的丰富性、音量的大小应该是最主要的素质指标。由此而言,没有一种乐器的表现力能和钢琴相比。钢琴可以演奏人声可及的全部音域,据说玛丽娅·凯莉(Mariah Carey)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唱遍七个8度的歌手,能唱出只有海豚才能发出的高音!钢琴就是能演奏七个8度的乐器。钢琴可以同时演奏不同的声部,可以同时发出不同声高的乐音,因此可以改编交响曲和歌剧作品来演奏,其他的乐器没有谁能做到这一点。钢琴的音量和音色变化之丰富也不是其他乐器可以比拟的。中国古琴虽然能弹出一百四十多个音,远多于钢琴,但音量和音色的变化就无法相提并论了。或许有人说,以这个标准管风琴岂不比钢琴表现力更强大,是的,毫无疑问。管风琴可奏出九个8度,可以模仿交响乐团各种乐器的声音,其表现力自然是超过钢琴的。但问题是管风琴似乎已不宜视为单件乐器。从管风琴诞生之日起,它要发出声音就需要多人同时操作,直到近年经过电子化的改造才简便了许多。一件能模仿各种乐器的乐器,就像现在的电子琴,可以代替一个乐队演奏,谁还将它看作是一件乐器呢?只能说是集多种乐器于一身了。如此看来,说钢琴是表现力最强大的乐器,应该没有问题吧?
以前在京都大学客座时,听平田昌司教授讲过一个笑话,说上课讲了半天后现代(postmodernism),快下课时问大家明不明白,有什么问题,一个学生弱弱地问:“那什么是现代(modernism)呢?”做老师最让人沮丧的经验就是,你要教给学生与学历水平相称的知识,结果你发现他们更需要的是补习更基础的知识。你要给硕士生讲唐诗的技巧和意境,结果发现他们连近体诗格律都不懂;你给博士生讲怎么写论文,结果论文交上来,首先要替他们改的是标点符号和注释格式。很难想象一个羽毛球选手进入少年队或青年队,连握拍的动作都不正确。为什么中文系的学生念到研究生了,还不懂得读唐诗和写论文的基本知识呢?看来我们的教和学两方面确实都存在不少缺失。
常人对音乐发烧友的理解就是追求完美声音的人,这是不对的。发烧友之痴迷于器材,一如吃货之于美食,不一定要高大上,而是追求品级范围内的完美效果。就像陆文夫《美食家》的主人公,大清早起来乘黄包车赶去吃头汤面,一碗阳春面也可以达到美食的上乘境界。美食乃是一种精神,发烧也是一种精神。没有所谓终极的完美,只有特定条件下的完美。家门口五块钱一碗的小馄饨可以有小馄饨的完美,名店350元一例的鲍鱼鸡也不一定有鲍鱼鸡的完美。条件有限,不如多投资于,器材差不多就行了。毕竟音乐,旅途中听听手机里的音乐也可以。一旦沉浸到音乐中,常会忽略效果,散步时甚至脑放也会很愉快,步幅都伴有韵律感。
看到布鲁诺的这句话:“当我们把上帝称作本原和原因时,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事物;当我们谈到自然中的本原和原因时,我们则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不同的事物。”(《论原因、本原与太一》)我恍然觉得他好像是在说西洋美术的焦点透视和中国美术的散点透视的差别。
潘德舆(1785-1839)的格言集《念石子》,介于清言和家训之间,很有些精彩的议论。其四十三则曰:“天下有使人信之道,而无使人必信之道。夫使人必信者是己疑人之不信也,己疑人之不信而人之不信至矣,是己启之也。故君子之信断疑,小人之信贼信。”此所谓“信之道”和“必信之道”,实际上就是真理和信仰的差别。真理是可以被质疑的,而信仰则不可以。因此能否被质疑,是真理和信仰的分水岭。可质疑的真理接近科学,不可质疑的信仰邻于宗教。这很大程度上验证了波普所说的,凡不可证伪的命题,就不是科学的。潘德舆说君子之信断疑,就是解决你的疑惑,通过证伪来使自己成立;小人之信贼信,则是一味玩弄别人对真理的信任,而不让人质疑,最终使真理流为盲目的信仰。一百八十年前的人,能具此认识,不能不说是真有灼见。
来源: 文汇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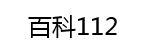 实操教程“玩呗麻将看牌器”(原来真的有挂)-抖音官网!" data-original="http://kexinwang.com/css/1.jpg" />
实操教程“玩呗麻将看牌器”(原来真的有挂)-抖音官网!" data-original="http://kexinwang.com/css/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