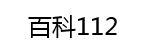7月,1000多万大学毕业生即将告别校园,踏上新的社会旅程。何谓良好大学生活?这个深刻的话题,对于每个读者来说,都亟需探讨。
大学是绝大多数人求取知识、完善人格的重要一站。当大学教育陷入困境,我们应该如何消除误解,重现大学教育的本质与价值?
因此,我们需要翻开这本小书,重思这个于我们至关重要的问题:从思想的、教育的、科学的、文化的角度感受大学的价值和重要性。
剑桥大学思想史教授斯蒂芬·科利尼坦诚之作《大学 ,有什么用?》,用一个核心问题,串联十个与之紧密相关的热点。面对社会主流对大学价值的诘问,斯蒂芬·科利尼勇为大学一辩,勇为人文教育一辩。
在本书中,他直面当今大学教育的困境,探究人文学科的本质;为我们悉心梳理英国大学的历史、人文学科的品格,并对目前“政府、公众与大学”的关系做了犀利的分析,并指出“在大学公司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它和当下的我们息息相关。
问某物有什么用(what something is for),到头来往往是自讨苦吃。首先,这么问有危险,它似乎把一项复杂的活动或一个复杂的机构,简化为单一而狭隘的用途。比方说,“爱有什么用”或“有什么用”,针对这类问题,任何简短而富于启发的答案都难免令人生疑,因为我们马上感觉到,这些答案总是混杂着使人厌倦的陈词滥调和个人的倾向性。
其次,这么问会招致一个后果,即任何答案都可能诱发同样的问题——“好吧,但那个又有什么用?”于是问题接二连三地抛出,没完没了。当推理之球开始沿着辩解的斜坡滚落,我们意识到,其可能的终点是一个淤积了抽象名词的烂泥塘,答案的特异性尽失;任何中间的停靠站都难免主观武断,故而易受影响,一旦有人轻轻一推,球的轨迹就会发生改变。这种状况使人想起一部老卡通片,里面描绘了一个桀骜不驯的早熟小孩,他双手抱住脑袋,双肘杵在厨房餐桌上,对站在身旁的恼怒家长说:“我只是观察到,你所说的‘因为A所以A’似乎包含一个隐藏的前提。”历史没有记录这个孩子后来是不是成了一名卓越的哲学家(或是否真的活到了成年)。
然而,若把某物的“作用”理解为一种解释策略、一个讨论起点而非最终裁断,那么这个问题不失为一种途径,帮我们清除任何被广泛使用的范畴周围堆积的杂乱无章的话语碎片。或许,正是这样略显执拗乃至咄咄逼人的提问方式,才能刺激我们反思,促使我们理清杂乱思绪,并思考如何做出有益的回应。因此,最明智的做法,可能不是对狭隘的问题穷追不舍,而是让思考自行蔓延,沉思可能被某个术语遮蔽的多样性,斟酌一系列的描述和界定方式,或揣摩种种历史实例,而非寻求单一的、决定性的观点。
毫无疑问,这将是本书采取的策略。如果所述的原初问题——“某物有什么用?”——有助于开启这样的一连串反思,让我们得以远离新闻故事和评论专栏里反复使用到令人麻木的陈词滥调,那么该问题就已经达到了它的目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经问道:“经济学有什么用?”他利用这个著名的问题提醒读者,追求财富本身不是目的,追求财富只是使人们过得“明智、愉快、安好”的手段而已。
毫不夸张地说,当下关于大学的公开讨论,基本可以简要归纳如下:大学若想获得更多资助,就得拿出正当理由,证明这些经费有助于大学赚更多钱。这样的观点令人沮丧。本书试图从别的角度入手,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谈论大学。
显而易见,我的论点可能招致误解和歪曲(我早前沿着这一思路进行论证时,曾遭受挫伤,至今仍未痊愈)。请允许我在这里申明:我相信,我和几乎所有在大学里工作、关心大学发展的人一样,从未低估大学的费用开支,也从未想当然地以为,大学得到巨额资助乃天经地义之事。人们当然需要论证大学的价值及重要性,但需采用适宜的论证方式,不能主要从经济的角度论证,更不能仅限于经济角度。我们还需要从思想的、教育的、科学和文化的角度去论证大学的价值和重要性。另外,必须强调,高等教育属于公共品,它带来公共利益,而不只为偶然参与其中的那些人提供私人福利。因此,在为大学辩护时,将之描绘为只代表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小群体事业或自利性质的事业,实乃谬论。
本书认为,倘若我们仅仅聚焦于经费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这一具有局限性和临时性的指标上,我们将无法辨识大学的独特品格。同样,有人认为思想探索是一种奢侈行为,其经济效益有待证明;基于这样的预设来谈论大学的价值,我们就无法真切地领悟思想探索的真正品格和趣味所在。若仅从当下对受教育机会或权利的关注切入,我们也无法充分理解,相对于其他形式的教育和培训,大学教育究竟包含什么,或者应该包含什么。“经费”“影响力”“受教育机会”成为讨论问题的出发点,它们时而单独出现,更多时候构成三位一体,表明个人立场的现实主义和与时俱进。无论以何种方式出现,这三个词完全主宰着今日英国政界和媒体就大学展开的公共讨论。实际上,这些都是次要议题,尤其是后两个词,它们只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套话,是政客针对某些社会态度所做的拙劣表达,因为他们觉得迎合这样的社会态度于自己有利。当我对这些时兴的词提出异议,如我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所做的那样,我所关注的是词语背后的种种隐含假设,而无意于(除非不经意为之)推荐可供替代的备选方案。
部分是本书的主体。我首先概述大学在当代社会的地位,然后在第二章中简论英国高校当前状况的历史成因。在第三章中,我先与约翰·亨利·纽曼的经典文本《大学之理念》展开对话,进而探讨“博雅教育”理念与提升人类理解力之间的关系。为使论证进一步深化,第四章着眼于人文学科的本质和作用。毋庸讳言,聚焦人文学科,不是因为我相信它们比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大学中占据更为核心的地位,而是因为人文学科的特质和价值通常没有后两者那般深入人心;另一个原因是,人文学科是我本人极为熟悉的领域。在第五章,我将与当下关于大学之功用的主流意见展开开诚布公的辩论。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采取了不同的论证策略:通过几则实例分析,我展示了,我们在对官方近年来出台的高校政策的批评中如何借机将关于大学的本质和作用的恰当说法渗入公共话语之中。总体而言,第二部分的各个章节篇幅更为短小,笔锋更为讥讽,观点更具投机性;它们力图把部分概述的宏大议题运用于当前的争论,犀利地回应时下的热门话题。此外,在第二部分的各个章节中,我们见证了历届政府——无论隶属于哪个党派——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如何以愈演愈烈的方式将经济议程强加于高校。
本书就大学所表达的见解,部分源自我对实践的反思,因此我应该在本书的开头指出我所亲身经验的实践。广义而言,我自己的写作和教学一直处于文学与历史的交叉领域。具体而言,我的工作主要关注英国19世纪和20世纪(现在也研究21世纪)的文学文化和思想文化的某些面向,包括英国高校的历史。假如我的学术背景是哲学或音乐、古典学或艺术史,那么我对大学的见解无疑会大不一样;假如我的学术背景是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某一领域,我对大学的见解可能会迥然不同。应当承认,我所借鉴的经验皆取自相对有利的工作环境。我1970年代中叶至1980年代中叶在萨塞克斯大学工作,随后来到剑桥大学,它们都是声誉卓著、(大体上)资助充裕的高校。我意识到,任何在这类机构工作的人都应当时刻牢记:教学和学术活动的开展,在别的高校可能遭遇大得多的限制和约束。
我相信本书探讨的诸多议题,在某些的高校中也颇为常见,因此我希望本书的观点能够在面临相似问题的别国读者那里引起共鸣。不过,本书的主题和实例主要源自我在英国高校的工作经验,相应地,我的论证方式力求参与当代英国就高校议题展开的公共辩论——我认为这并无不妥。我所表达的见解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别国的高校、切合它们那里关于大学的公共辩论,恐怕只能交由对此有更多认知的专家来定夺。我多年来就英国高等教育所撰写的文章,常常获得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积极回应,这让我觉得,找到富于启发的相似点并非难事。
《大学,有什么用?》既不是官方的白皮书,也不是哲学专著。它最接近的文类是论辩文(polemic),而后者则与讽刺文学、哀诉文学、宣言,以及文化批评领域的论说文(essay)等文类多有重合。这些文类与读者订立的契约,建立在说服力这一原则之上。它们并不试图通过逻辑上的不可辩驳(logical indefeasibility)或实证上的无所不包而强迫读者赞同认可,它们的论据也并不依赖于完美可行的提议。相反,这些文类旨在吸引读者去关注、辨识那些迄今为止被人忽视的、被不实描述的、被低估或被压制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辨识过程总是诉诸读者已经一定程度了解的东西——否则,所描述之物就不会被真正辨识出来。我希望诸位读者会觉得这本书既长见识,又令人信服。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读者能从中辨识出一个能打动自己的关于大学存在的理据,唤醒半掩埋于内心深处的关于大学宗旨的直觉,进而宣扬这一大学宗旨,使之在公共领域产生影响。
本文节选自《大学,有什么用?》,有删改